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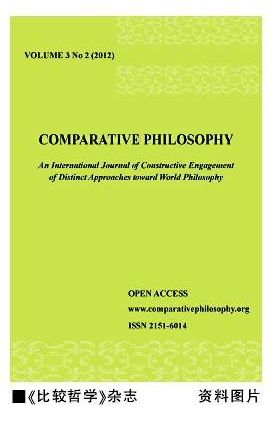
“比較哲學”這一術語常在一種既狹義又廣義的理解下使用。其狹義就以下兩方面而論:第一,以往這一詞項往往僅指來自植根於不同民族/文化/地理區域傳統的思想傳統或哲學傳統(如西方傳統、中國傳統、印度傳統等)的不同思路和觀點的比較研究﹔第二,在“比較哲學”名義下的工作,有時止於歷史描述性的考察而非進一步的深層哲學思考,例如,在對歷史事實作描述性比較而刻畫一些表面現象上的差異和相似時,對於深層哲學意義以及這種差異和相似對我們今天理解和處理哲學問題如何能有建設性貢獻,則要麼沒有觸及,要麼不了了之。這種情況以往常出現在專門從事漢學、歷史學、宗教學、文學或亞洲研究的學者的這種“比較哲學”研究工作中。與上述第二點相聯系的是,在對中國哲學研究中,以往常將比較哲學視為中國哲學研究的副產品,即當這種研究論及與其他哲學傳統類似觀點時以“中學為體”的立場而順帶地“比較”描述一番。就其寬泛含義而論,在進行那種歷史描述性橫向考察時,往往文史哲宗兼論,沒有根據哲學解釋和哲學問題的目的與需要而深化相關哲學材料的考察。
自21世紀初以來,以一種哲學上有意義的方式所理解和從事的比較哲學在國際哲學界崛起發展,並在如下含義上成為一般性哲學探索的前沿:即探索那些來自不同哲學傳統、不同方法論風格取向的不同思路、方法、眼光、洞察、基本觀點、概念性、解釋性資源,以期通過反思性批評而相互學習,為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哲學上有趣和有意義的問題協同互補地作出建設性貢獻。這種含義的比較哲學研究一方面強調反思批評和自我批評,另一方面強調如此的目的是為了相互學習並為共同的哲學事業作出貢獻。強調反思批評和建設性探索的比較哲學研究策略不妨用刻畫和突出上述特征的“建設性交鋒—交融”(constructive engagement)一詞來表征。這種含義上的比較哲學研究,不局限於僅關注來自與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相聯系的不同哲學傳統的不同思路或觀點,也包括來自有不同風格/方法論取向所表征的哲學傳統的不同思路或觀點——后者可能是跨民族文化傳統的,如廣義理解下的分析哲學與大陸哲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因此,這種比較哲學研究更具有哲學上的一般意義,並拓寬了某些傳統理解下過窄的方面,如不受限於僅考察來自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不同哲學思想、不止步於純考據性或純歷史性描述。但同時其收“窄”了某些在傳統理解下過寬的方面,如專注於哲學研究而非不加區別地文史哲宗兼收並論。在上述含義上,這種哲學上的比較研究在性質上、目的上和方法上不同於或有別於比較宗教學、比較歷史學或比較文學中的比較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強調哲學上建設性交鋒—交融的比較哲學研究並不否認或忽略歷史描述性工作的相關性和必要性,並不把這種歷史描述性工作本身排除在比較哲學研究工作之外,也並不否定研究者可以根據個人的學術興趣、訓練背景和所指派研究任務之性質等而畢生或在某一階段專注於歷史資料收集、歷史描述或史料考據。一方面,這種歷史描述性“比較”工作可以是一項比較哲學探索項目的資料匯集或階段性工作,它對於比較哲學探索是相關的、必要的﹔另一方面,哲學上的比較哲學研究在整體上(或就其反思重點而論)不止於這種歷史描述性工作,而在於解釋和思考不同思路和觀點對於我們今天理解和處理哲學問題如何能有積極的建設性貢獻。
一般來說,在這種哲學上有趣、對哲學發展具有建設性和創造性意義的比較哲學研究包括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可以說是“對象探索”層面﹔另一個層面則是“元哲學探索”層面。在“對象探索”層面,通過哲學問題意識和哲學解釋,比較哲學具體地探討關於某一研究專題所論及的若干不同思路和觀點如何能對於共同關注的哲學問題以某種相容互補的方式作出建設性貢獻。正是通過哲學問題意識和哲學解釋,在比較哲學“對象探索”層面上關於某一哲學問題或論題的若干原來看似不相關的不同思路和觀點才變得相關,從而得以在共同關注的哲學問題上交鋒,進而使我們有可能探討它們中的合理因素以作出建設性貢獻。在“元哲學探索”層面,比較哲學研究明確地、一般性地乃至系統地關注和探索如何看待來自不同哲學傳統或哲學研究的不同風格或取向及其不同實質性觀點或概念/解釋性資源之間關系所涉及的一系列元哲學、元方法論問題,諸如如何看待來自不同哲學傳統或哲學研究的不同風格或取向的不同方法論立場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之間關系的方法論引導原則(methodological guiding principles)及其適當性條件。所謂“哲學研究的比較哲學方法”,關注的正是上述兩個層面的具有一般哲學方法論意義的比較哲學研究。
(作者單位:美國加州聖荷塞州立大學哲學系)
(責編:秦華)
 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行【詳細】
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行【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