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儒敏,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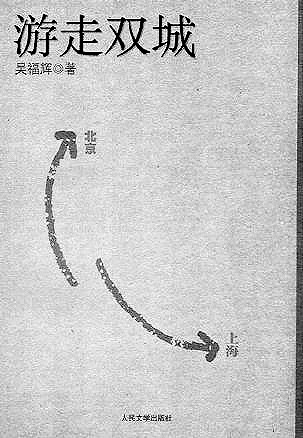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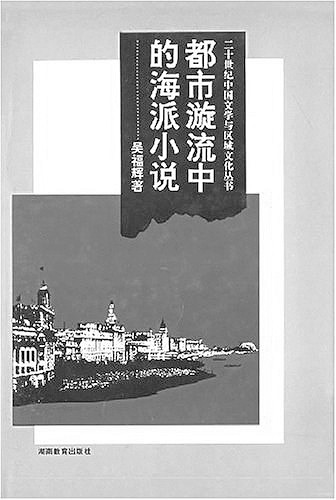


吴福辉(右)与青年学者交谈。
学人小传
吴福辉(1939—2021),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文学史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著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沙汀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等。
时光飞逝,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是2021年春在加拿大家中过世的,现在拿起笔来写这篇回忆,仍然非常悲恸,眼前满是这位老同学的斑驳影子。
记得他去加拿大之前一个月,我还去潘家园看望过他,那时他已患肠疾多年,越发衰瘦,正翻箱倒柜收拾北京的房子,准备去加拿大和儿子过。我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他解释了几句,便是苦笑,默然。我们又一起去东四吃馆子,他胃口还挺好,兴致又来了,说以后还会回来看看的。我想这怕是很难了。到加拿大以后,彼此联系就很少。我们有一个同学微信群,老吴偶尔也会“冒泡”。我是不太看微信的,直到他去世后几天,才从“群”里知道一些事。
他去加拿大后仍然肠病缠身,动过大手术1次、小手术3次,病况略有好转。2020年岁末,他过81岁生日那天,还照了一张相,是站在一个门框前边,两手交叉胸前,露出的笑容,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灿烂了。他还写了一首《自寿诗》,是发给老同学张中的:“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万户门。雪岭松直正二度,平屋笔闲又一春。窗前狗吠车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丝冬意暖,犹念旧日芳满庭。”这是老吴的绝笔?可想他在异乡是多么思念旧日往事!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从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我和老吴结交了43年。如今他“潇洒”远去三年了,我还能为老同学做点什么?就写点文字吧。这两天把老吴送我的著作都翻了翻,结合自己平时积累的感受与印象,“研究”一下这位老兄。
一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就留校教中学,教得很好,后来还“官”至教导主任。吴福辉是极聪明的,读书很多也很杂。后来他回忆自己的“阅读史”,青少年时代就涉猎过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这种“量级”的广泛阅读,培养了他的文学爱好,也培养了他的形象思维包括直觉思维。他的艺术感受力很强,跟青少年时期“无目的”的大量阅读,是有关系的。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所培养的感受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文学青年”的“杂览”经历,真的喜欢文学,不只是由于职业的需要而阅读,这些都是吴福辉日后把文学研究作为志业的良好基础。
吴福辉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投射并促进了他的研究。他是浙江镇海人,自小在上海长大。小学毕业时,父亲被调到东北去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鞍山,从此他就长作“关外人”。他讲的是地道圆润的东北话,若遇见上海老乡,立马又是一口纯正的沪语。他所写的各种文字,涉及东北的并不多,倒是有关上海的,源源不绝。可见,幼年的上海生活记忆,已经非常深刻地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因为后来长期远离上海,越发构成印象的强烈反差。吴福辉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非常细腻真切地回忆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爱文义路四寿村家居的生活情形,连那种声响、气味似乎都还能感受到。吴福辉后来读张爱玲,特别关注的也是张爱玲笔下老上海的生活情味,还专门为此写过七八万字的“看张”——《旧时上海文化地图》,什么居住、街市、店铺、饮食、衣饰、娱乐、茶场、婚礼等,叙说中浸透着老吴浓浓的乡情,尽管这个“乡”是大上海的“城”。为什么后来老吴那么津津有味研究“海派文学”?为什么格外关注市民通俗小说?跟他幼时的生活经历积淀以及后来因异地迁徙而“放大”有关。都说吴福辉是“南人北相”,上海始终是他梦萦魂绕的家乡,也就成为他文学研究的源泉。借用鲁迅《朝花夕拾》的话来说,老吴的许多研究都源于“思乡的蛊惑”。
吴福辉幼时在上海的生活比较优裕,后来去了鞍山,在这个中等城市的郊区生活、上学、教书,同学大都是矿工子弟或农民子弟。他因此感到过“落差”,但也因此而获益,他比许多从学校到学校的文学研究者更切身地感受到基层社会的生活情状。
老吴酷爱自由,感情丰富,爱玩、爱吃、爱旅游、爱交友,爱收藏各种奇石,文学研究只能说是他多种生活爱好中的一种,他能在其中获得独有的成就感和乐趣。北大中文系给吴福辉的唁电中称赞他“风清气正,机智有情,流而有节,惠学及人”,我看是恰切的。老吴为人忠厚、和气、低调,这体现在他的研究中,就是极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批判,也不太在意“意义”“价值”,但很能见出他对生活的热情与兴致。他研究“海派”,研究“市民通俗文学”,都侧重生活样貌和质感,表现出宽容与理解。
老吴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长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数十年中,他接触过很多第一手资料,认识和访问过很多文艺界的元老和名家,可谓见多识广,也形成了审美的多样性和生活化。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随性自在的,自由放达的。如大家都叫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若没有文学馆资料丰厚和他见多识广的背景,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他居然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此书采取了适合他自由个性的那种漫谈式结构,就如同一位导游领着读者在现代文学“地理”的各个角落漫游和欣赏,多的是史料、趣闻、细节。大家从未见过这样散漫而有趣的文学史,这是吴福辉的成功。
还有一点特别要说说,就是吴福辉的大多数著作不属于什么项目,也没有资助,他就自己放开手脚去做。像《沙汀传》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都是做了四五年才完成。我曾写文章批评现今学界艰难而烦躁,是因为不少人都被项目和计划所牵绊,处于“项目化生存”的状态。有多少题目真是自己有兴趣的?不过是为了“中标”或者某些实际利益而操作罢了。这一点老吴就占了“便宜”,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自选动作”,而并非计划内的“项目”。研究吴福辉,以及吴福辉这一代学者,应当考虑这个因素。
二
下面,再说说吴福辉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有四个方面很突出,是会给后来者所记取的。
第一个贡献,是参与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是研究生毕业就被分配去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那时现代文学馆八字还没有一撇,他们先是在沙滩老北大红楼附近的地震棚上班。我听老吴说过,最初只有4个人,三个老同志,只有吴福辉是“专业人士”。后来经巴金呼吁、胡乔木协调,借了紫竹院公园边上的万寿寺做筹办的办公室,人员也陆续增加了杨犁、舒乙、刘麟、董炳月等。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访问作家,收集、抢救资料。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破旧的院落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他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写作高峰期。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成了现代文学界最活跃的角色之一。文学馆后来也就搬到朝阳区新址。老吴在文学馆一待就是30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巨大的。
我特别要说说他刚去文学馆那几年,和杨犁等主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选编重点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家,共有708人,每位作家都有一个小传,附上作品的书目。那时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几乎人手一册,影响很大。现在年轻的学者未必了解,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其实是从编“作家辞典”开始的。在吴福辉这本辞典之前,已经有北京语言学院老师编过《中国文学家辞典》,其中也收有很多现代作家。老吴这部辞典集中在现代作家,非常详尽。这项工作几乎从零开始,难度是很大的。以“辞典”的形式让一大批被误解、埋没的作家重新得到评价,这本身就是“拨乱反正”。现在看来此书只是工具书,在当时其实功莫大焉。
吴福辉的第二个贡献,是“海派文学”研究。“海派”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不是个方向相对一致的文学流派,而是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特殊环境里产生的样貌多元而又显示出某些共同特色的文学潮流。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就有过“京派”“海派”之争,注重文学趣味与道德感的沈从文,曾把上海一些作家命名为“海派”,认为其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甚至把当时左翼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也归入“海派”,后来还引起一段论争。沈从文是从“京派”的立场观看“海派”,有明显的偏颇,但他显然说出了当时存在“海派”这一事实。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对于“海派”根本不提,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文学史也都没有“海派”的位置。直到八十年代末,严家炎做小说流派研究,第一次给“新感觉派”命名,并以专章论说,“海派”的一部分才成了“出土文物”被发掘出来。而吴福辉审时度势,几乎也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他对“海派”小说的专门研究。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就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海派”文学的著作,学界已经有很多评论,这里就不展开谈论了。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不见得最早,却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而且从他开始,“海派文学”这个名词就在文学史论著中“登堂入室”了。
大家未必意识到在“海派”文学方面有更大影响的,是吴福辉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写的相关部分。该书的1985年上海文艺版给了“新感觉派”和徐訏、无名氏的小说专门两节论述,并小心翼翼冠名“洋场小说”。到1998年该书做了很大的修订,就专门打出“海派小说”的名堂,给予专节论述。其中概述了“海派”小说世俗化与商业化,过渡性地描写都市等特点,论及的作家除了新感觉派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还有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禾金、黑婴等等。“海派”从此正式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地位,而这部分是吴福辉写的。后来有关“海派”文学的研究多起来了,可以说是吴福辉带了这个头,他的“海派文学”研究不但领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标杆。
吴福辉的第三个贡献,是市民通俗小说研究。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大本营应当是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是领军的人物,最早呼吁把通俗文学写进文学史。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年出版。但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时,就曾专门辟出三章来叙述“通俗小说”,其中涉及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等等。这是第一次把“通俗小说”融入综合性的文学史,并给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这部分工作是吴福辉承担的。2016年该书第三次修订,改动很多,有些章节几乎重写,其中改得最多的就是老吴写的“市民通俗小说”三章。老吴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也很看重,还把重写的三章收到他的《石斋语痕二集》中。我知道很多老师使用这本教材时,大概不把“通俗小说”纳入教学计划,但作为一本完整的现代文学史,“通俗文学”的有机融入,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这三章是很难写的。通俗文学作品太多,要从中选择,还要加以评论,得下相当大的功夫。
吴福辉的第四方面贡献,是提出“大文学史”观,并尝试写成《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文学史是可以不断重写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可能也应该出现不同写法的文学史。十多年前,学界有过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反思,普遍对以往文学史叙事方式表示不满:那就是常见的从“五四”前后开始,以时间为“经”,文体与作家作品为“纬”,突出代表性作家评论的模式。这种书写方式以教科书功能的考虑为主,有意无意都想写成文学的“正史”。这种“不满”由于受到历史学界“新历史主义”的启发而引起新的想象,希望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凸显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等多种关系,由过去围绕单一“中心”的文学作品解构策略,转为多中心或者无中心的历史状态叙述。那时就出现关于文学史写法的多种设想。诸如“文学生态说”(严家炎)、“雅俗双翅论”(范伯群)、“先锋与常态说”(陈思和)、“重绘文学地图”(杨义)、“民国文学”(李怡等)等。这些想法角度各不相同,也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如何落实?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于是就有吴福辉的大胆尝试,他很包容地提出“大文学史”概念。他倡导“合力型”文学史,把文学史看作文化场域中多元共生的文学变化史。他还借用王瑶先生的说法,做学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一个观点为主,如同一张唱片转圈子,发出声音;另一种是叙述多个观点,发散型的,如同织毛衣,一针一针地织,再一块一块地连缀起来。吴福辉就采用“织毛衣”的办法,用三四年时间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这部文学史让大家耳目一新,因为从未见过如此结构,也从未见过如此丰富的内容。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以及作家的生存条件、迁徙、流动,社团流派的活动等,全都囊括其中,一条一条叙述,一块一块铺陈,试图构成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加上丰富的资料罗列,名家逸事的安插,年表、大事记的罗列,特别是大量的插图,让人读起来有点像逛博物馆。
这部文学史是“散点叙事”,去“中心”化,以及有意淡化作家作品的分析,读完以后似乎目迷五色,抓不住要点,自然有它的偏颇,但毕竟是大胆的尝试,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史,也可以说是对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后来吴福辉还与朋友合作,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线索,采用编年的书话体来结构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文学史的叙述与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虽有趣,却驳杂琐碎,不得要领,未见得达成所谓“全方位的立体的文学全景的效果”。无论如何,吴福辉“晚年变法”,不是坐而论道,也很少在理论上与人交锋,他就实干,以一人之力放手去写,终于写成了“插图本”这部气象万千、非常好看的“大文学史”。此书你也许可以挑出这个那个“不足”,却又读得有滋有味,不得不佩服。
吴福辉是个坚实、卓越而低调的学者,他给现代文学研究作出很大贡献,后来者能从他的著述中获益甚多。他以82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是在大洋彼岸,那个冰雪覆盖的地方辞世的,也还是那么“低调”。据他的家属说,老吴是睡梦中猝发心脏病过世的,可谓“善终”。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学来说,这多少也就有点宽慰吧。
图片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涛及吴福辉之女吴晨提供
学人自述
我1959年于辽宁的中学执教,到1978年重新进校门读研究生,算是“老童生”了。考取的六人中倒有五人具备在中学(中专)教书的经历。但我又稍有些特别,因为我当年无缘进正规大学读本科。所以说起我的特点,第一位的就是靠“自学”。这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弱点。
自学的人多半有“终身学习”的习惯。我少时有许多爱好,喜欢下棋、打乒乓球、画画、唱歌,后来为了看书,都淡化掉了。课外的文学阅读是我最大的乐趣。我记得《老残游记》是在一次旅途的车厢里,蜷缩在行李架子上读的,其时大概五年级。初师、中师阶段赶上了使用四册《文学》课本的时代,从《诗经》一直读到《小二黑结婚》,等于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压缩本。当然不满足,就在课外猛读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涉猎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过几百部苏俄的小说,连类而及法、德、英、美和鲁迅提倡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自学”造成我的“杂”和“正统”。
“自学”还让我学会了设计自己。国家有国家的大目标,我有我的小目标。我读马卡连柯的教育小说和教育理论,那里有一个“明日欢喜论”颇得我心。可能现在看来属于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吧,但我几十年来全靠这前面的光亮支持。我的生活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郊区乡镇,我不觉得有多么苦,我无法厌弃这点光亮。我起先的学习是围绕“当一个语文教育专家”设计的,所以包括中外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教师基本功等,有一整套的自修计划。
由于“自学”,我独立读书的能力比较强。我在当中学教师期间,读现代文学作品,读资料,读理论,读文学史。读史是比较靠后的,是在独立读了大量作家作品有了识别能力之后进行的“小结”。这是我1978年经一个月的复习能够考取研究生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我多年的自学,就为这次考试无意中做了准备。后来我不止一次地说,1978年的那次考试好像就是为我举行似的,我等它等得好久、好苦。但是看看现在,我们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往往不会创造性地阅读,却塞了一脑门子的文学史的常识和结论,这成了他们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障碍。
我的研究生学习尽管还是以自学为主,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北大拓宽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的思路。校风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是无形无踪的。我最初写的“五四”小说理论批评的论文被导师不软不硬地碰回来,心里多日不好受,现在看就是应有之磨难。我由此明白了王瑶先生那句“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熟了一点”,等于说你不过是用别人的材料在谈别人的观点罢了。这与北大的学风不合。我是从此才下决心每写一篇论文,必须用心发现自己寻觅到的材料,独创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的。这种自主独立的学术风格,是我与我的天才的老师们、同学们,在数年时间里反复、相互碰撞中绝大的收获。
——摘编自吴福辉《看一粒粒萤火在前》,载于《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