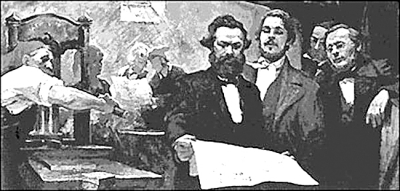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編輯部。 (油畫) 薩皮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一脈相承,不可分割。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法治思想,對於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必有助益。本欄目將陸續登載此類文章,和讀者一起探尋經典作家筆下的法治思想精髓。
馬克思是一位法學科班出身的思想家。他於1818年5月5日出生於普魯士邦萊茵省一個猶太律師家庭。1835年10月,進入波恩大學法律系學習﹔一年后,轉學入柏林大學法律系,1841年3月畢業。馬克思寫於1842年初的第一篇政論性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也是一篇法學專論。同年4月,馬克思為科隆《萊茵報》撰稿,后任該報主編,直到1843年3月17日退出該報編輯部。馬克思早期積極地參與了當時社會生活中一些重大法律問題的討論,闡述了一系列法學觀點。
其一,法律隻應當追究人的行為。馬克思認為,人要要求生存權,要求現實的權利,就必須通過自己的行為來進行。“只是由於我表現自己,只是由於踏入現實的領域,我才進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圍。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因此,行為是人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領域。
其二,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馬克思早期從理性法、自由法觀念出發,論証了自由與法的關系,提出命題:“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一方面,強調法律的根本任務是維護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另一方面,自由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因為法律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馬克思的這一命題還有強調法律神聖性的意思。如果法典能夠像《聖經》那樣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引、提供依靠,那麼,法律的信仰就有望形成了。
其三,法律應該適應事物的本質。馬克思早期接受了自然法學派特別是孟德斯鳩的思想,將法律和法區分開來。他圍繞這一觀念,表達了自己的法律觀點。首先,立法者不是在制造、發明法律,僅僅是在表述法律。“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識的實在法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出來。”這一論述體現了馬克思對法律與法的關系的初步認識,即立法不能違背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其次,法律應該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意志所創立。再次,法律的背后是利益問題。“結果利益所得票數超過了法的票數……凡是在法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讓私人利益為法制定法律。”顯然,馬克思當時已初步看清了國家和法的本質。
其四,國家有義務制定良法。馬克思認為,國家有義務制定良好的法律。如果法律不好,就會給人民帶來災禍﹔如果公民犯了罪,隻有國家才能給予懲罰。懲罰犯罪既是國家的權利,又是國家的義務。國家不能放棄自己的義務。如果放棄了自己的義務,就等於國家犯了罪,因此是一種罪行。
其五,懲罰權是國家的專有權。馬克思主張“公眾懲罰”,反對“私人懲罰”。他認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客體是國家保護的某種社會關系,因此,懲罰權是國家專有權,不能轉讓給私人。他還繼承和發展了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思想,根據行為是犯罪構成和刑罰的基礎這一觀點,主張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其六,關於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系。他把程序法與實體法譬喻為植物的外形和植物,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關系,一個是生命的形式,一個是生命的內容。他提出,實體法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訴訟形式。例如中國法裡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紀刑律的內容連在一起的訴訟形式一定是拷問,以此類推,自由的公開審判程序,是那種本質上公開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屬性。他由此得出結論: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是法律的內部生命的表現,所以,程序法和實體法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
其七,關於立法和司法的關系。馬克思基於對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關系的認識,提出:“如果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了保証法律能夠正確地實施,馬克思主張,法官應該以法律為准繩,獨立地進行審判。同時,他反對司法專橫,闡明了在刑事案件中應當實行自由的公開審判程序。
其八,法院判決的離婚隻能是婚姻內部崩潰的記錄。馬克思認為,婚姻的本質是一種世俗倫理關系,婚姻是家庭的基礎,離婚不能聽憑個人的任性,不要把任性提升為法律。正由於婚姻是家庭的基礎,所以才成為立法的對象。因此,離婚不能僅注意夫妻雙方的主觀意志,尤其不能遷就個人任性,而應服從婚姻關系的本質或內在規律。
馬克思在早期把自由和理性作為分析法律現象、探討法律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理性法、自由法觀念像一根紅線,貫穿於馬克思早期的法學著作之中。馬克思早期的法學思想邁出了從唯心主義的理性法律觀過渡到歷史唯物主義法律觀的第一步。沒有馬克思早期的法律觀,也就不會有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西南政法大學政治學法學理論研究基地聯席主任,西南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