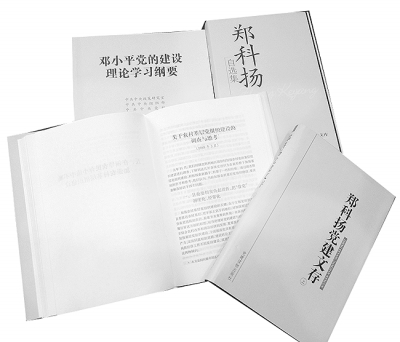
鄭科揚部分著作 楊謐攝

資料照片

鄭科揚與夫人稅蔚蓮結婚照 資料照片
“今天的中國,完全超越了我青少年時的夢想。”坐在北京市朝陽區一間普通居室裡,著名黨建研究專家鄭科揚回憶過往,神採飛揚。“我離休了,但沒有離黨。我願意一直為黨工作,迎接建黨100周年,甚至新中國成立100周年。”
83歲的鄭科揚,黨齡已有67年。從進步青年到地下黨員,從黨政干部到理論專家,他經風歷雨、飽受磨礪,卻始終抱持著一個不變的信念: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不二之選,研究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是自己的神聖使命和“人生樂事”。
“我一生最重大的根本性轉折,從此開始了”
鄭科揚青年時代最難忘的日子,是1947年6月的一個星期三下午。那日,江油高中學生鄭科揚請假不成,就翻越學校圍牆,按規定時間來到一戶農民家中,在他的入黨介紹人和一位縣委委員見証下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遵守黨章,服從組織,嚴守紀律,嚴守秘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永不叛黨。”
一切都在秘密進行,卻絲毫壓抑不了鄭科揚對未來“新天地”的熱情向往。
他清晰地記得,一個夜晚,高年級一位同學介紹他入黨時的初次談話。
“你品學兼優,我想介紹你參加一個組織。”
“什麼組織?是不是共產黨?”
“你先別問,但我可以告訴你,這個組織現在的目的是推翻國民黨統治,解放勞苦大眾。”
“那就夠了,我參加!”
從入黨那天起,鄭科揚的人生歷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把主要精力用於組織學校黨員搞學運、辦壁報、鬧學潮,支持進步老師排演《棠棣之花》《升官圖》等話劇,揭露反動政府的腐敗,宣傳革命思想。他以校學生會主席的身份為掩護做了許多工作,也在革命斗爭中迎來了自己的愛情,與同班同學稅蔚蓮走到了一起,相伴至今。
更大的變化,是內心信仰的逐漸清晰。
鄭科揚少年坎坷。父親開了間賣麻制品的小店,一家人勉強度日。后來轉營煙酒,境況略微寬紓,卻先遭祖母、母親相繼離世,后遇鄰家失火蔓延至自家,多年積蓄基本化為灰燼。堅強勤勉的父親很快走出痛苦,與人合伙把綢緞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然而,苦難沒有放過這個家庭,1946年,父親故去,留下鄭科揚兄弟姐妹8人。大哥接過父親的鋪子后不久,被人欺騙、投資失利,將家產盡數賠光。此后,幺妹夭折,幺弟送人,骨肉離散。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為保存軍力,不惜犧牲人民生命財產,制造花園口決堤等事件。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政府又挑起旨在消滅共產黨的內戰,弄得百業凋敝、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社會動蕩。雖家在川西北的小鎮,鄭科揚還是耳聞目睹農民抗糧抗丁、工人游行罷工、市民商人抗稅罷市,學生罷課等情景。這一切使他深刻感受到: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人民極度貧困、社會急劇動蕩,就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朽、無能。
他曾試圖從書籍中尋求解決問題之道。小時候,鄭科揚熟讀《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和四書等等,懷抱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願望。可是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實現願望、改變社會的道路在哪裡?
在迷茫中,他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引。
“什麼是共產主義?當時還很懵懂。但是認准了一點:要建立人民政權,‘解放勞苦大眾’,就不會錯。”鄭科揚坦言。
真正了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始於1948年春上級送來的一篇文章和一本書。文章題為《自由主義者的畫像》(后來鄭科揚才知道就是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書是列昂節夫著的《政治經濟學》。鄭科揚秘密地讀完了他們,方知人民的困苦來自於剝削和壓迫,而剝削和壓迫來自社會經濟制度,來自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制度,以及維護制度的統治階級。他開始明白,推翻蔣介石政府並不是最終目的,目的是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頭腦一旦清醒,步子就更堅定。我一生最重大的根本性轉折,從此開始了。”
“‘不行就學!’還是不行就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四川臨近解放。這時,國民黨瘋狂抓捕進步人士,大肆殺害共產黨人。年僅18歲的鄭科揚和其他9名共產黨員,經黨組織做上層統戰工作,進入國民黨地方武裝任上尉指導員,任務是掌握部隊,迎接解放,降低損失,度過黎明前的黑暗。他利用機會,抓緊工作,很快掌控了這支一百多人的部隊。江油縣解放前夕,國民黨派的中隊長趁亂逃匿,鄭科揚當機立斷,率隊佔領了中壩鎮郵電大樓﹔又封鎖城門,阻擊國民黨潰軍,不讓他們入城搶掠。解放后,鄭科揚按照縣委指示,將部隊整編后,改為縣警衛營的一個連。不久,由於工作需要,他轉到縣委機關工作,參加了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群眾運動中“經風雨、見世面、受鍛煉”。
生活並不總如諜戰劇般精彩。1959年,鄭科揚從共青團綿陽地委書記的崗位走上了另一條重要而清苦的戰線——理論和研究工作。
1958年,毛主席鑒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經驗教訓,提出要重視理論學習和理論工作,要求各省(市、區)各辦一個理論刊物。四川省委主辦的《上游》雜志,調鄭科揚任編輯。兩年后,黨中央決定,從幾個大區選調一批年輕人到中央機關有關部門作為理論工作后備人才培養,鄭科揚也在其列,被分配至中央宣傳部理論處。
巨大的挑戰很快顯現出來。鄭科揚上崗不久,就感到吃力和焦灼——一方面,理論工作做什麼,怎麼做?未經過系統訓練的他並不清楚。另一方面,由於理論功底薄,隻讀過少量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工作時別人講得頭頭是道,他卻聽得雲山霧罩。
深感壓力的他,硬著頭皮去找領導吐苦水:“我的素質和能力干不了理論工作,是不是調錯人了?還是放我回四川吧。”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許立群通過理論處處長給出了答復:“不行就學。”
簡單的四個字,斬釘截鐵,一語點醒了鄭科揚:“‘不行就學!’還是不行就跑?”“跑”算什麼共產黨員!他選擇了學。
一邊埋頭啃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一邊閱讀於光遠、蘇星的《政治經濟學》、艾思奇的《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讀物,對毛澤東著作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格外用心。在中宣部的前3年,鄭科揚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學習。他讀完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全集》,還帶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讀完了《綱鑒易知錄》。其時,夫人仍在四川農村鍛煉,鄭科揚帶著兩個孩子在北京生活。每天晚上,他先將孩子哄睡,然后洗衣、縫補,做畢家事,才能安心讀書至深夜。這種勤學深研的精神,不但使鄭科揚逐漸在理論領域得心應手,也成為他畢生不變的學風與作風。
“做黨和人民需要的理論工作者”
鄭科揚一直以“做黨和人民需要的理論工作者”來要求自己,也深深記得“文革”過后心靈上的一次震動。
1978年,中央組織部籌辦部刊《組工通訊》,當時已調至中組部的鄭科揚被任命為部刊處處長。6月1日,《組工通訊》第一期剛發出,就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為推動撥亂反正,我們編發了一篇評論,題目是‘抓緊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其中提出‘凡是搞錯了的案件,做錯了的結論,不論是誰搞的,尤其是自己經辦的,都要以黨的利益為重,該否定的堅決否定,該糾正的堅決糾正’。各方面反應非常強烈,有贊揚,也有責難,甚至稱其為‘翻案文章’”。
這時,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同志特意召見鄭科揚,把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中的一段話逐字逐句念給他聽:“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這段鄭科揚早已熟知的話,再次而且永遠地印在了鄭科揚的腦海中,成為他做理論工作的准繩。
其實,對鄭科揚來說,這樣的風波並不陌生,在他的工作生涯中,已經經歷過三次。
反右派運動、“文革”初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末期“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鄭科揚均受到牽連、批判。歷史進程的反復,個人發展的緩滯,沒能消磨鄭科揚的心志。每每遭遇挫折,他都更願意反思自我。及至如今,他依然時常回顧自己的過去,自察省身。他認為,個人的遭遇同黨在探索前進中的挫折分不開,一個黨員不應因此怨人怨黨,而應汲取經驗教訓:“黨在頑強探索中前進,我們也在一步步懂得真理。馬克思主義原著是真理,但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回答當今面臨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隻能在探索創新、不斷前進中尋求解答。”
積極的心態,坦蕩的胸懷,實事求是的風格,讓鄭科揚的理論之路走得更為堅實。1983年,鄭科揚由中組部部刊處處長直接擔任研究室主任,其后歷任中組部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研究員,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等職。在參加或負責起草文件、撰寫講話、整理研究領導人著作等龐雜事務面前,鄭科揚從未放棄了解實情、研究和思考問題的習慣。如今,我們可從《鄭科揚黨建文存》《鄭科揚自選集》中一窺他當年的思想脈絡。之所以將文集稱作“文存”,鄭科揚另有深意:“這些文章成書出版時,我盡可能保持原狀,就是為了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檢驗我過去的看法和認識。”
他的文章,始終貫穿著“大黨建”的觀點與視角,在學界影響深遠。
“我長期在中央分管黨建工作的領導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潛移默化地培養了我的全局意識。研究黨的建設,決不能目光短淺、視野狹窄,就黨建論黨建。研究黨建,必須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變化,以及整個世界形勢。孤立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孤立研究執政黨建設,都不可能正確認識或回答面臨的問題。”鄭科揚認為,所有的黨建問題,都應圍繞三大問題展開研究:舉什麼旗,怎麼舉好﹔走什麼道路,怎麼走得順當﹔執政后為誰掌權,怎麼正確用權。
從“大黨建”的視角出發,他和十幾位同志一起,在鄧小平理論中解讀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執政黨建設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相互融合的黨建科學體系。上世紀90年代,他們精心研究、梳理出版了《鄧小平黨的建設理論學習綱要》,很受歡迎。今天,這仍是他不斷研究和思考的一大領域。
“理論工作絕不能脫離實際。實踐出真知,群眾是英雄,基層有創造”
滿頭白發,輕裝簡從。2014年4月,鄭科揚的身影出現在四川省綿陽市游仙區魏城鎮鐵爐村。走訪村辦產業、詢問基層黨建做法、看望為帶領村民致富獻出生命的“好支書”張勇家人。年逾八旬的老人深入調研,一絲不苟,還不時記錄著什麼。
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這是鄭科揚從青年時期就注意鍛煉的基本功。進入中宣部前的14年中,鄭科揚大多數時間在基層工作,深感人民群眾的實踐對於理論研究不可或缺。胡耀邦曾對他諄諄勉勵:“‘實踐豐富多彩,生活之樹常青’……隻要你們眼睛向下,留心觀察現實生活,就會發現有做不完的題目、寫不完的文章。”親身感受和領導勉勵,令他更加注重向基層、向群眾、向下級學習。2000年,從一線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鄭科揚,終於有機會用更多時間下基層調研了。他從東、南到西、北,從鄉村到企業、社區,考察著一個個黨建發展的鮮活“樣本”,提交出一份份厚重扎實的調研報告,得到黨中央和有關部門領導的重視。
他還記得重慶九龍坡海龍村一位普普通通的村支書。2010年秋,鄭科揚赴海龍村調研,一跨進村展覽室,就被牆上貼著的一篇短文吸引了。文章是幾年前村支書自己寫的,標題是《小崗之行話發展》。小崗村帶動了全國農村改革,很快解決了溫飽問題,但為什麼“一夜邁過溫飽線,20年進不了小康門”?村支書提出問題,並找到了三條原因:經濟結構單一﹔集體經濟不強﹔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不夠。於是,村支書從海龍村實際出發,採取措施,發動群眾,村中面貌在8年間發生了巨變。
“這是來自基層的科學認識和實踐創新,值得我們贊揚、學習。可見,理論工作絕不能脫離實際,實踐出真知,群眾是英雄,基層有創造。這是我在基層調研時一次又一次的切身感受。”鄭科揚感慨不已。
這幾年,他把一些典型村落、企業視為聯系點,多次前去。在湖北襄陽,他更深地理解了農村基層黨組織怎樣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東方控股集團,他感受到了先富的共產黨員怎樣保持和發揮先進性的感人之處﹔在四川江油市星火村,他看到了黨組織怎樣抓住災后重建的機遇,激發農民的“兩個積極性”,引導群眾走共同富裕之路。現在,很多村民、企業家、工人把他當成自家人,結下了深厚情誼。
基層調研的經歷與心得,令鄭科揚更加深感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04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啟動之后,鄭科揚擔任咨詢委員會委員。在他心目中,為理論工作添磚加瓦,是職責所在、使命所系。為了這一工程,十年來,盡管他一邊擔負著全國黨建研究會、全國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專業委員會、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課題等多項工作,一邊悉心照顧纏綿病榻30載的發妻,卻從未對工程書稿審定、參加會議等工作推諉敷衍。任務重時,他依然如年輕人般深夜伏案,一字一句地寫下審讀意見與修改建議。
“我希望,這項工程能長久地抓下去,隻能加強不能削弱。要有問題意識,加強對矛盾、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同時加強隊伍建設、拓展對外交流,把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更好地用起來、傳出去。”鄭老的建議如此殷切。
記者詢問鄭科揚如何自我評價,他興致頗高地翻出了一本詩冊:“袁寶華同志90大壽時,曾寫詩贈我,我也和詩一首,或許這首詩可以回答你的問題。”言畢,他一字一句地念出了這首《答袁公》:“九旬賦詩非自嘲,略抒文採令人陶。思敏身捷老當少,壯志若昔信念牢。國運中興正展俏,願與蒼生共歡笑。名利更比浮塵小,甘作紅燭我盡燒。”
(專家名片:鄭科揚,著名黨建研究專家。1931年7月出生於四川江油。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歷任中組部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研究員,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組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本報記者 楊 謐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