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離,系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西省作協副主席

傅修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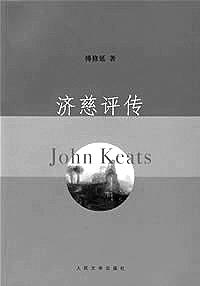
傅修延著《濟慈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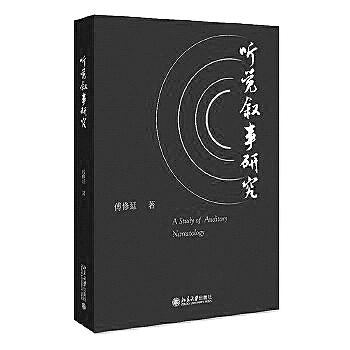
傅修延著《聽覺敘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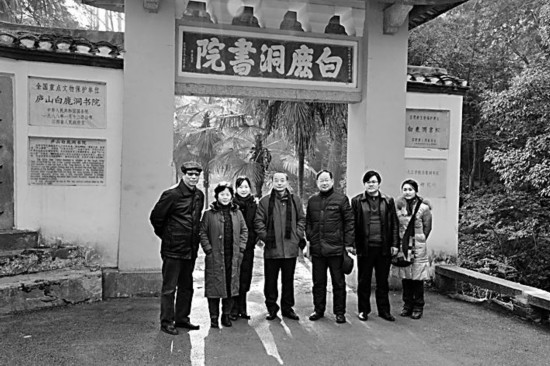
傅修延(右3)與友人在白鹿洞書院。
學人小傳
傅修延,江西鉛山人,1951年生於江西南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工作室首席專家、江西師范大學資深教授。1977年考入江西師范大學外語系,1979年被破格錄取為該校中文系研究生,后獲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揚州大學博士學位。先后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做訪問學者。曾任江西師范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著有《濟慈詩歌與詩論的現代價值》《中國敘事學》《聽覺敘事研究》等,主編“中西敘事傳統比較研究”叢書。
一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江西曾是人文昌盛之地。但是到了近代,贛鄱大地亦歷盡滄桑。但物華天寶之地,人杰地靈之鄉,總有人志存高遠而又腳踏實地,有足夠的耐心又有足夠的毅力,堅持不懈,奮勇向前,辛勤耕耘,終於結出了碩果。傅修延便是這類江西人的代表。
提起傅修延,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敘事學研究。20世紀90年代初,傅修延從多倫多大學訪學歸來,出版了他的敘事學處女作《講故事的奧秘》。那時候,敘事學不像今天這樣熱門,還被一些習慣了將“敘事”與“抒情”並列的人視為故弄玄虛。但傅修延並沒有在意這些,因為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成立,最終取決於它能不能滿足時代和現實的需要。今天,敘事學已經成了一種被廣泛運用的跨學科理論,這顯示了他的先見之明。
要全面理解傅修延敘事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也許需要更多的時間。因為雖然年過古稀,傅修延卻仍處在令人驚訝的學術生產火山噴發期(這一點他自己用“學問於人有精神滋養之功”來解釋),2024年他主編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七卷本“中西敘事傳統比較研究”出版。他當然具備很多優秀學者的共性,比如視野開闊、知識淵博、感受敏銳、心思專注和精力旺盛等,但他可能更有其他學者所沒有的一些特異品質。比如他對世界永遠有一種孩童般的強烈好奇心。這種好奇心讓他對於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有著異常強烈的探索願望和動機,而沒有這樣的願望與動機,一個人不可能在學術研究上做出真正有意義和價值的發現,因為任何發現都是好奇心、想象力和創造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一場學術演講后,有人問傅修延,人類精神能否在賽博空間永存?他回答,多年前自己就在想這個問題,他每年的日記少說也有十多萬字,加上著述和其他文字,這些儲存在電腦中的東西便成了個人記憶與經驗的物化,將來人們可以憑借這些信息,與大數據中永不消逝的“我”進行互動。講座結束后著名符號學家趙毅衡立即發來微信:你預言人類精神將在大數據中永生,這個觀點把我們都“驚到了”。事實上傅修延這種把人“驚到了”的先鋒觀點還有許多,例如當前人們都在努力學習使用AI,他卻在《敘事的本質》中說人不能淪為機器的奴隸,“動物精神”仍然是人們做選擇時的決定性因素。又如學界對“后人類”問題的討論甚為熱烈,他卻在《從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中說今人尚未完全實現對自身心智的主宰,理由是許多敘事作品都提到人物能聽到大腦裡的另一個聲音。再如人工智能的強勢崛起讓不少人文學者感到前景迷茫,他卻在演講中說AI對人腦的模仿處在人類早期模仿文化的歷史延長線上,因此“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才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我們讀他的學術研究著作和文章,有一種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很會講故事。他的文章寫得特別吸引人,那些非常專門的、在局外人看來有點枯燥的專業問題,到了他的筆下,變得趣味盎然、引人入勝,例如他寫過一篇名為《嗅覺敘事與中國倫理話語的形成》的論文,引發大眾的興趣。他從來都不願“為學術而學術”,不會做“鄰貓生子”之類的無聊學問,更不會以莫測高深的高頭講章來唬人。所以即使在學術研究的范疇之內,他筆下的文字也是讓人感到親切,有著令人難忘的情感溫度。文品即人品,一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生,在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方法論熱潮中嶄露頭角的學者,到今天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無論是為人還是為學,都有一種難得的敞亮的“少年氣”,這不僅令人羨慕,更令人深思。
二
按照傅修延自己的說法,如果沒有走上治學的道路,那麼他在今天很有可能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莫言演講和本雅明著作都用過此名)。根據我的理解,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戲言。有人看到他分析刀郎歌詞藝術的隨筆,感嘆說此人在文學創作上有極高的天賦和才能,如果不是被學問“耽誤”了,他該會創作出多麼了不起的文學作品啊!可能他自己內心深處有時候也會有某種遺憾吧,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很有限,你選擇了一條道路,就會錯過另一條道路上的諸多美景。
這樣來看待他的學術研究,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其中既有思想的真知,又有情感的溫度。他是一位特別有“現實感”的學者。對於書齋中工作的學者來說,如果缺乏“現實感”,他的所有研究就可能變成一種從概念到概念的思想空轉,無法與這個世界及他人生活發生有意義的關聯。傅修延與歷史上那些富於現實關懷的贛地先賢一樣,對自己的生身立命之地懷有深厚的情感,著文發聲更接地氣更有擔當,這是他特別令人敬重和佩服的地方。
他本科就讀的是外語系,隻讀了不到兩年,便被破格錄取為中文系的外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當時允許這樣做)。雖然學的是外國文學,但他首先是一位腳踏華夏大地的學者,外國文學研究在他那裡一直被定位為“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也就是中國人對外國文學的研究不能簡單重復外國人自己的研究——他的原話是“如果我們這邊說出來的話,和人家那邊說出來的話一模一樣,那就不是中國的或者說不是中國人的外國文學研究”。具體到敘事學領域,他之所以舉起“中國敘事學”這面旗幟,是因為看到一些西方學者罔顧華夏為故事大國、中華民族有數千年敘事經驗之事實,試圖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國的情況下總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敘事理論。結構主義敘事學當年在歸納“敘事語法”上陷於困境,視野狹窄便是一個重要原因。
處於后發位置的中國學者確實應當虛心向先行一步的西方學者學習,但西方敘事學主要植根於西方的敘事實踐,其理論依據很少越出西歐與北美的范圍,在此情況下,中國學者應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敘事傳統,並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上描述中西敘事傳統各自的形成軌跡,以及相互之間的沖突與激蕩,如此敘事學方能成長為更具廣泛基礎、更具“世界文學”意味的學科。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同行表現出對此觀點的認可。
按照我的理解,這就是很多年以來,傅修延為什麼要那樣著力培養和扶持一大批后起學人的原因。他身邊圍繞著一批性格不同才能各異的中青年學者,他首先以自己身體力行的學術實踐,成了他們的示范者和引領者。2012年,卸下了行政職務的傅修延,每周四晚上,都會在江西師范大學那幢名為“王字樓”的木結構老房子裡主持敘事學讀書會,時長達兩個半小時,參加人數通常都在30來人。這個讀書會雷打不動地堅持了十多年,有位讀書會成員如此表達自己的感受:“每周四與師友圍坐一桌,言笑晏晏,長了見識,增了知識,真乃凡塵中桃花源。”
學界有個說法,一個科研團隊既要有人“指兔子”,又要有人“打兔子”和“撿兔子”,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成功。2022年江西師范大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家敘事學研究院,毫無疑問,研究院的首席專家傅修延就是“指兔子”的人,但他又要求團隊成員不能總在自己的舒適區“打兔子”,而是要滿世界去“找兔子”。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大多受過系統的外語訓練,有相當嫻熟的中外文獻檢索功夫,一些人還有在歐美學習工作的經歷,這就使得他們的研究具有一種既“知己”又“知彼”的優勢。在與年輕學者的交流中,他經常引述王國維的“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還說要向珠江入海口的基圍蝦學習——這種蝦漲潮時喝咸水,退潮時喝淡水,做學問也應該這樣“咸淡水通吃”,也就是擁有開放的胸襟,既懂中國的學問,也能消化外國的知識。國際敘事學研究會會長馬可·卡拉喬洛在最近一次與傅修延的學術對談中,表示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基圍蝦之喻:“我們都應該暫時擁抱自己內心的‘基圍蝦’,通過成為‘他者’(甚至是非人的存在),以更全面地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復雜世界。”
三
中西敘事傳統比較屬於比較文學范疇,傅修延為這項研究投入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得出了許多富於創見的結論。然而,不應該僅僅將他的研究看作是對本民族敘事傳統的捍衛,而應該理解為他對真理和真知的執著追求。知識讓人靠近真理,隻有和真理站在一起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如果說傅修延的學術研究有著一般學者所不具備的格局和境界,原因應當向此處尋找。
讓我們來看看他對敘事傳統的中西差異是怎麼解釋的吧。他倡導聽覺敘事研究,是因為他發現中國文化以聽覺來統攝包括視覺在內的各種感知,而西方文化強調“以視為知”(看到才是知道),也就是說中西文化在視覺和聽覺上各有倚重。以敘事學家最為關注的事件展開方式為例,趨向明朗的西式結構觀(源自亞裡士多德)要求保持事件之間顯性和緊密的連接,順次展開的事件序列之中不能有任何不相連續的地方﹔而趨向隱晦的中式結構觀則允許事件之間的連接可以像“草蛇灰線”那樣虛虛實實斷斷續續。用文化差異來解釋敘事並不新鮮,像傅修延這樣從感覺倚重角度入手卻是首次。中國敘事經典的“尚簡”“趨晦”和“從散”等特征,隻有與聽覺的模糊性聯系起來,才能理得順並說得通,將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感知途徑影響信息傳播)這一思路引入研究,一些與中西敘事傳統有關的問題因此獲得了更加貫通周詳、更具理論深度的解答。
敘事學領域內像中西差異這樣的重要問題還有不少。以敘事的本質為例,西方敘事學家對此雖有涉及但隻作了迂回式的側面探索,他卻對這個問題展開了正面強攻,以一篇五萬字的長文《敘事的本質》對此展開了全方位論述,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學界重視。他的《文學是“人學”也是“物學”》《元敘事與太陽神話》《人類為什麼要講故事》和《人類是“敘事人”嗎》等論文,光從題目上也可看出“其志不在小”。他總是以自己的敏銳、睿智和擔當,直面那些他認為不能留給后人去解答的大問題,同時結合自己的知識積累和生命體悟,調動起自己所有的思想資源,發揮出自己最大的想象能力和創造能力,努力給出自己這一代學人所能給出的最優答案。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傅修延的著述中隻有難啃的硬邦邦理論,讀者大多認為他的文字讀來親切感人,其行文能將深奧的專業探討化為娓娓道來令人如沐春風的“拉家常”。雖然涉及的問題非常重要,但他從來不會板起面孔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善於從衣食住行等生活日常出發,對人們天天看到但又未去細想的現象去做深入發掘。讓一些循規蹈矩者難以想象的是,他竟把面容作為符號學的研究對象(《論作為能指的面容》),又從絲巾追溯到體現中國審美特質的飄帶精神(《絲巾與中國文藝精神》),還試圖用耳朵去感知敦煌壁畫(《從“聽感視覺”角度認識敦煌壁畫》)。由於這些探討充滿妙趣,他后來干脆出版了一部《趣味敘事學》。前面提到他稱學術於人有精神滋養之功,至此我們明白,為什麼一些人覺得苦不堪言的學術研究,在他那裡竟像是孩童在沙灘上玩自己的游戲。
傅修延的女兒傅真是一位作家,她在文章中稱父親為“一個很妙的人”,並列舉了這個“妙人”在日常生活中許多異想天開的舉動。借用這個說法,我們可以說隻有像他這樣的“妙人”,才能寫出上述那些“妙文”,而“妙文”之中又不能缺少“妙語”和“金句”。我看到有同行引用他談面容中的話:“人之為人在於有一張被內在精神‘照耀’的臉。人類可以用無數創造物來証明自己的優秀,但最好的証明還是自己這副經歷了漫長演化過程的面容。”我自己特別喜歡的則是絲巾文章裡的一節文字:“絲巾是可收可放、可揮可甩和可執可舞的,又是可系可解、可折可疊和可包裹又可被收納的,人們無法想象這小小的織物,居然擁有如此之多的可能性,而正是這些可能性賦予其靈性、自足和超脫等形而上特質。”
如今,在短視頻和語音信息的反復“投喂”之下,文字駕馭能力成了一種“稀缺物質”,許多人已經不會組織清晰流暢的文句了,傅修延那些行雲流水般的精妙表達顯得特別可貴。如果要問這樣的能力從何而來,除了大量的書寫實踐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對祖國文化與民族語言的熱愛。很多人不知道這位外國文學學者還擁有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學位論文《先秦敘事研究》后記中有這樣一番話:“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我感到自己越來越趨向本民族的文化,內心深處‘我是中國人’的聲音越來越響亮……用拉丁字母表達的一切,對我來說遠遠不如用方塊漢字敘述的東西來得親切有味。”
話雖這般說,為了讓中國學界的聲音傳到西方,他還是會用拉丁字母來與國際同行互動。中文系文學專業的人,大都想把文章發在國內的頂級期刊上,而他不僅做到了這些,還在《文體》(Style)、《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評論》(Neohelicon)等著名國際期刊上發表過文章,《文體》及《敘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語言與文學》(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國際期刊還有對其研究的評論與訪談。他的《中國敘事學》(英譯本)在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入選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聽覺敘事研究》不久后也將由這家出版社推出。
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同行常常顯得拘謹,傅修延卻不在此列。Neohelicon的主編匈牙利學者彼得·海居請他給自己的敘事學著作寫序,傅修延在序言中直言,不能把中國敘事傳統視為另類,否則就有滑向“歐洲中心論”之嫌。不過他又說,自己和對方是有多年學術交往的“好兄弟”,“好兄弟”之間就是要這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從1983年發表《〈項鏈〉的鏈形結構》算起,傅修延深耕敘事學已有四十年之久,今天稱他為敘事學家似不為過,但我更想說他的身體裡面還住著一名詩人,或者說他因早年研究《夜鶯頌》作者濟慈而擁有一顆詩心。他為這位早夭的浪漫天才奉獻了三本書:翻譯了40萬字的濟慈書信,寫出了國內第一部濟慈評傳(為此遍訪詩人足跡所及之地),研究濟慈的專著《濟慈詩歌與詩論的現代價值》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在《濟慈書信集》的譯序中,他稱“愛是不能忘記的,學術研究上的‘初戀’同樣銘心刻骨”。他的女兒名字中有一個“真”字(來自濟慈《希臘古瓮頌》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也讓我們理解他為什麼會帶領妻兒去羅馬的濟慈墓前獻花。詩人在天之靈仿佛感應到了異國知音的到來,《濟慈評傳》后記如此描述:“去新教公墓的路上細雨如絲,走進公墓后雨絲如同被突然剪斷,一道陽光從雲層裡射出,照亮了墓地與其后的古城牆與金字塔,走出公墓后雨珠又開始滴落。”
傅修延對濟慈的情有獨鐘,可能緣於這位詩人不像拜倫、雪萊那樣出身貴族,也不像華茲華斯、柯勒律治上過劍橋牛津,當時一些批評家勢利眼,把他視作地位低賤的“倫敦佬”。傅修延小學二年級時便隨父母到江西弋陽縣農村生活,1968年初中未畢業的他到新建縣的朱港農場工作,在血吸虫肆虐的鄱陽湖水域開過三年船,從船工轉到新余冶金機修廠當起重搬運工后,還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工傷事故:他從15米高的車間屋頂跌下,導致嚴重腦震蕩、內臟大出血和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大難不死的經歷讓他對命途多舛的濟慈懷有強烈共情,但詩人對他影響最大之處,還在於“在人世間這個‘淚之谷’中始終綻開燦爛的笑顏”。在探究濟慈內心時,人們深感欽佩而又為之傷痛的就是這種情懷,它有一種巨大的感染力,使人更加熱愛生活,更加努力去追求生命中一切有價值的事物。
傅修延和濟慈一樣,不管命運如何虧負自己,從來沒有失去過對生活的希望,也沒有失去那種追求人間美好事物的激情。我們在其妙趣橫生的文字中感受到的一切,歸根結底都可以追蹤到濟慈對他的這種影響。蔣勛有句話放在這裡可能比較合適:一個人心裡有青春,那他就可以一直處在青春期。正是因為胸中一直懷有這樣的青春激情,他才會在農場和工廠中一直堅持自學英語、刻苦寫作,幾乎沒有半點懈怠,所以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復,他便以優異成績考進了江西師范學院(即后來的江西師范大學,當時他這樣的“大齡”考生只能報考省內高校,而該年江西招收英語本科的隻有這所學校)﹔也是因為前期基礎相當扎實,他才能在進大學不到兩年后又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四
行文至此要說點文學之外但又離得不太遠的話。傅修延是最早提出“贛文化”這一概念的江西學者之一,后來他又覺得“贛鄱文化”這一名稱更為合適,因為國內其他地域文化(巴蜀、齊魯和燕趙文化等)也是採用這種雙子星座式的表達,“贛”與“鄱”的激蕩匯合反映出江西這片土地的勃勃生氣。他在省社科院院長任上提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倡議,這個倡議后來被採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現在已成為國家級經濟區。他提議過在南昌建利瑪竇廣場,理由是利瑪竇在這裡待過三年,與江西讀書人多有交往,這可以顯示豫章城是中西文化碰撞並濺擊出明亮火花的地方。許多朋友還記得,他曾大聲疾呼在南昌鬧市原址恢復萬壽宮,如今重建的萬壽宮及相鄰街區已成為游客必來打卡的觀光勝地。他在本世紀初提出以白鶴為江西省的省鳥,20年后得到省人大常委會正式批准。需要說明,他關注白鶴,是因為憑借自己的比較文學知識背景,看出南昌地方文獻上記載的浴仙池故事(女主人公為白鶴仙女)實際上屬於全球廣泛傳播的羽衣仙女傳說,文化部門因此認定他為該傳說的“非遺”傳承人。還有他對贛菜過辣過咸的批評,以及“重口味”可能導致地域文化粗鄙化的思考,引起過贛地諸多有識之士的共鳴。他帶的兩名博士生曾經不理解導師為什麼硬要自己“改行”做景德鎮瓷繪研究,如今在陶瓷敘事領域中收獲滿滿的她們,說起當年的“被逼迫”來,充滿了感激。
最后要提到他為打造江西師大瑤湖新校區傾注的心血。2009年省裡把他從社科院調回江西師大擔任黨委書記兼校長,這種“一肩挑”的安排意味著他要承擔起償還基建貸款以及為工程掃尾的全部責任。在此過程中,他以文化人獨有的藝術想象力,為校園增添了一系列景觀亮點。來到這裡,人們會驚喜地發現,校園沒有圍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國內獨一無二、環繞三千畝校區的護校河,沿著護校河還鋪有一條長逾5公裡的健康小道,此外還有鐘樓、桃李鼎和一幢古色古香的書院建筑。當人們表示贊賞此類舉措時,他卻說要感謝時代把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給予了自己:作為高等教育中人,能夠親身經歷中國大學這種跨越式發展,這讓自己在回顧往事時有一種不枉此生之感。
前面提到,傅修延說在治學上要像基圍蝦那樣“咸淡水通吃”,這裡我們看到他對學問和事功也取一種兼顧態度。不過我想他可能更願意把自己看成是來鄱陽湖越冬的白鶴,這種鳥兒既會在濕地的泥漿裡埋頭啄食,又能飛上藍天發出“聲聞九皋”的清越鳴聲。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