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暢,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詞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

郁賢皓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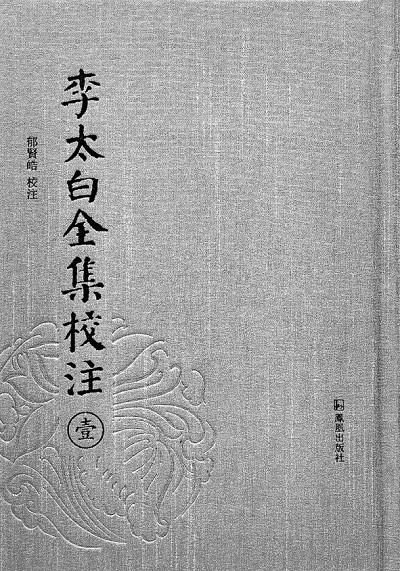
郁賢皓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郁賢皓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郁賢皓,1933年生,上海人。1961年畢業於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師范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所長,曾兼任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有《李白叢考》《唐刺史考》《李太白全集校注》等。
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收藏著一套郁賢皓先生捐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捐贈時間是2021年5月。這部2016年出版的著作,是郁先生畢生研究李白的結晶。翻開贈書,他批閱、修改的筆跡觸目皆是。可以想見,從此書出版到捐贈的5年間,當時已年過八旬的郁先生,仍然在孜孜不倦地修訂著自己的著作。
在有著“江南文樞”之譽的南京師范大學,郁賢皓先生是繼孫望、唐圭璋、段熙仲、錢仲聯等老先生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之一。他從李白研究入手,於唐代文學、唐代歷史研究中遨游,碩果累累。
章黃后學
郁賢皓先生1933年生於上海,少年失學,12歲就到上海光華電業制造廠當工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做過文書、干事,還做了幾年新聞工作,積累了扎實的文字功底。1957年,郁先生考入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走上學術之路。
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在孫望先生的主持下,南師中文系匯聚了不少古典文學名家。孫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學求學,得到黃侃、胡光煒、吳梅、商承祚、胡翔東等先生指導,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郁先生師從孫先生,在治學方向和治學方法上都受到孫先生影響。孫先生經常教導學生:“要為自己選定一兩部書,准備花畢生最大的精力去從事研究。要有勇氣在這一兩部書的鑽研中取得度越前人的成果,具有獨創的見解。”郁先生一生精研李白,其學術方向的選擇正源於此。孫先生極欣賞清代乾嘉學派腳踏實地的考証方法,認為“無論搞詩文的注釋分析,或者搞詩人作家的年譜,都離不開考証。做學問必須對作家的每一個交游設立專案,從各有關書籍中找材料,憑借史料分析、考証,才能得出正確結論,才能‘知人論世’,在此基礎上寫出的文章才是堅實的。”(郁賢皓《道德文章皆吾師:介紹孫望先生》)同在南師中文系任教的徐復先生,是章太炎、黃侃的嫡傳弟子,同樣重視考証,推崇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郁先生的李白研究重視作家交游、注重細節考証,就是受到了這種學風的影響。1961年,郁先生畢業留校,教古代漢語,繼續研讀清代朴學家著述,並旁聽南京大學黃淬伯先生講《一切經音義》、洪誠先生講《古書疑義舉例》,夯實了小學基本功。1963年,因徐復先生推薦,郁先生受邀參與《辭海》修訂工作,1965年修訂完畢。1973年《辭海》繼續修訂時,郁先生參與“示”部至“羊”部的修訂和審定工作。此后《辭海》歷次修訂,郁先生都作為編委兼分科主編參與其中。
1978年,孫望先生的大學同學、著名文學史家程千帆先生受聘至南京大學任教,住處離郁先生家很近。當年冬天,郁先生便隨孫先生拜訪了程先生。郁先生介紹了自己當時的研究工作,程先生告訴他:“做教師不能隻做教書匠,教書是為了培養人,培養人首先要不斷提高自己,所以還要做學問。做學問首先要腳踏實地搜集資料,對資料進行排比考証,你的做法是對的。第二步才是在考証的基礎上從事理論研究。”“有的人隻做第一步的工作,不做第二步的工作,是可以的。有的人隻做第二步的工作,第一步的工作不做,則斷斷乎不可。”程先生這裡說的“第一步”工作,是指全面仔細梳理研究對象的所有資料。程先生的鼓勵,讓郁先生充滿信心,此后經常上門求教。
鐘情李白
郁賢皓先生對李白研究情有獨鐘。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出於對李白及其詩歌的愛好,郁先生對此書中關於李白的部分認真讀了好幾遍,“我覺得其中有不少精辟見解,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那時的李白研究,多局限於詩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分析,對李白的生平事跡和交游缺乏深入稽考,未能做到知人論世,因此對作品的理解多流於主觀臆測,破綻百出”。當時,學術界對於李白的出生地、一入長安還是兩入長安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論,直接影響了對李白作品的分析和理解。於是,郁先生決定把李白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從考証李白的生平事跡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點和難點。他認為:“如果宏觀的理論研究沒有大量的微觀的實証研究的成果作為基礎,那宏觀的‘理論’必然流於空論,甚至會出現錯誤的結論。”
改革開放后,郁先生陸續發表十余篇論文,從不同角度研究李白的事跡與交游。1982年,這些文章被結集為《李白叢考》一書,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作為“唐代文學研究叢書”的第一種出版,這也是郁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他自己評價該書:“通過深入考証,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訂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為正確地深入研究李白生平思想和作品打下了一定基礎。”
《李白叢考》証實了李白一生“兩入長安”。20世紀60年代以前,學界一般認為李白一生隻到過長安一次,即天寶元年(742年)秋奉詔入京待詔翰林,天寶三載(744年)春離開長安。1962年以后,逐漸有學者質疑該結論,並提出“兩入長安”的觀點。郁先生的《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等論文,剖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西入秦海,一觀國風”一語,解析李白詩作《以詩代書答元丹丘》中的“三見秦草綠”,將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的情感表達與張九齡《張說墓志》參証,又通過李白多篇詩作分析出兩次入長安的時間與路徑差異,得出結論:李白於開元年間第一次入長安,停留三年,於天寶年間第二次入長安,僅停留一年。在現存李白詩篇中,有的作於終南山隱居之時,有的作於邠州、坊州應酬之際,這些作品均作於開元年間第一次入長安之時。彼時李白未求得官位,故自由往來於長安周邊,非天寶年間入長安之事。郁先生從五個方面証實了李白兩入長安的時間和路徑,使兩入長安之說得到實証。郁先生自己說:“李白兩入長安的發現與被普遍承認,不僅解決了李白生平事跡中的一個難題,而且對李白許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須重新研究,乃至李白的創作道路也必須為之改寫。”在此之前,學者在李白一入長安的背景下,將《蜀道難》《梁甫吟》《將進酒》《行路難》《梁園吟》等詩系於天寶三載(744年)之后。隨著“兩入長安”說的成立,學界對於李白詩歌的創作歷程有了全新理解。
對李白交游的考証,是郁先生李白研究中創獲最多的領域。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與宋之悌、道士吳筠等人的關系上。《李白詩〈江夏別宋之悌〉系年辨誤》一文推翻了將《江夏別宋之悌》系於肅宗乾元元年(758年)的錯誤,並指出宋之悌乃初唐詩人宋之問季弟,卒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前。可知李白在此時就已經創作出工穩的五言律詩,他的五律不是直到人生晚期才成熟。《舊唐書·李白傳》記載:“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郁先生在《吳筠薦李白說辨疑》一文中,結合李白自己的文章以及其他史料,指出“筠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有誤,進而指出李白於天寶年間待詔翰林乃玉真公主之薦。
郁先生對李白生平事跡、交游對象的考察,既補正了史料記載,也為研究李白詩風發展提供了可靠材料。
以對李白生平、交游的研究為基礎,郁先生開始了對李白詩文的整理工作,刪偽補遺、校勘、箋注、評箋,於是就有了《李太白全集校注》。此書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參校諸本以及歷代總集。郁先生將自己的新觀點、新發現都融入每篇詩文前后的“題解”“校記”“注釋”“評箋”“按語”之中。《古風》“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句,郁先生的按語是:“此詩當為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游洛陽時所作。據《舊唐書·玄宗紀》記載,開元二十二年己丑,玄宗幸東都,由此可知是年春天百官在東都上朝全為寫實。第一段寫陽春三月,天津橋邊千家萬戶桃李盛開,鮮花艷麗,動人心魄……”這種細致的解析,離不開深厚的史學、文獻學基礎。
由文入史
在研究李白的過程中,郁先生發現:“唐人詩篇中提到的交游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詩的寫作年代,很難深入理解詩意。”他由此想到可以編一部唐代地方長官的工具書,這一學術計劃得到程千帆先生的極力贊同:“這確實是學術界非常需要的書。唐代有許多詩人當過刺史,詩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隻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果能把名字考出來,考出此人的事跡,那就是對學術界很大的貢獻了。這樣的書,研究唐代文學、唐代歷史、唐代社會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先生還建議將此書定名為《唐刺史考》。
1987年,《唐刺史考》出版,“全時全地”地對唐代地方行政長官的姓名、任職時間、行跡進行考察。在時間上,此書所考列州刺史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與唐代國祚相當。在地域方面,此書基本涵蓋了唐代所有州郡。在編撰理念上,郁先生不僅注重傳世文獻,也注重出土文獻,大量引用唐人墓志拓片。為了搜求這些墓志拓片,他曾到南京圖書館請版本目錄學家杜信孚先生幫忙,“他聽了我的來意,很快就把我所需要的《芒洛塚墓遺文》等石刻資料書一一拿了出來。他還告訴我,館內藏有《千唐志齋藏石》拓片,近些年幾乎沒有人查閱過,說著,就熱情地把沾滿灰塵的幾捆拓片都搬了出來交給我閱讀。這些拓片雖然缺了二十多張,但使我從中獲得了許多重要資料。”1983年暑假,郁先生帶著助手方義兵到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查閱隋唐五代墓志拓片,二人連續工作十余天,將館藏的一千多張隋唐五代墓志拓片翻閱完畢,摘錄了大量資料。《唐刺史考》所引用的這些墓志文獻,為學界提供了許多便利。
《唐刺史考》出版后,郁先生又開始對其進行增補,經十余年艱苦精研,於2000年出版了《唐刺史考全編》。此書補充搜羅了十余年中新出土的唐代文獻,對其加以整理、排列、考訂,訂正了原書百余處錯誤,新增2000多個刺史的任職情況。
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杜牧、韓愈等諸多唐代詩人,都做過地方官。利用《唐刺史考全編》,讀者對於這些詩人的生平履歷,一檢即得,並可以由此考察他們的交游情況。《唐刺史考全編》考証出崔玄亮長慶三年(823年)至寶歷元年(825年)為湖州刺史,由此即可確定白居易多篇詩作中的“崔湖州”都是崔玄亮。因此,此書雖為史學著作,但對文學研究也很有幫助。
在文獻研究方面,《唐刺史考全編》匯集了各種唐代史料,將眾多唐代州郡長官的資料搜羅殆盡,並對引用的每一條文獻資料都進行比較鑒別,以判定其真偽,訂正了史籍中的一些錯誤,這使得該書成為閱讀、研究唐代史料的重要文獻。
在郁先生的著作中,與《唐刺史考》並稱的是《唐九卿考》。該書的編撰與他考証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一詩中的“衛尉張卿”有關。他回憶說:“當時我就想,唐代職官的工具書已有《新唐書·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唐方鎮年表》,當時我已在從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書,可以給學人查稽九卿帶來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於是自此以后,我就對唐代九卿的資料加以留意,在從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時,在野史、雜錄、金石、方志等文獻中,凡遇到唐代九卿的資料,都做成卡片。”郁先生與其弟子胡可先在廣泛搜集歷史文獻、金石文獻、文學、方志別乘等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對唐代九寺正卿與少卿予以考証、辨析,對九卿的歷史演變、職能變革、人員調整以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系等問題進行研究,填補了唐史研究的一個空白。
在文學、史學研究之外,郁賢皓先生還整理了《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一書。《元和姓纂》是研究唐代人物姓氏的典籍,原書散逸已久,今本由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史學家岑仲勉於1948年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記》。原文與校記分行,學者利用極為不便。1982年3月,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傅璇琮先生致函郁先生,請他對《元和姓纂》進行整理。傅先生了解郁先生的李白研究,確信他適合整理此書。郁先生深知《元和姓纂》《元和姓纂四校記》對唐史研究的重要性,故欣然接受此任務。經他與陶敏教授多年努力,1994年,經孫望先生審訂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記)》整理本終於告竣,此書至今仍是唐代文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朴學之風
作為章黃后學,郁先生無論在什麼領域鑽研,都注重實証,用文獻說話。
他研究李白,首先把李白的詩文作品熟讀,在閱讀的過程中,還寫下了札記,“將李白詩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並將姓名按四角號碼排列編制成索引,將卡片裝訂成活頁冊。然后認真地閱讀各種資料,從唐人別集到各種筆記,從姓氏書到宋元方志,從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發現有關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寫進卡片中去。”在《李白選集》一書中,郁先生對所選錄的三百余首李白詩、十余篇李白文,均作了校訂、注釋和編年。李白詩作抒情性強,可以編年的線索不多,但郁先生精心梳理,使諸多文獻得以綜合利用,並結合詩文的主旨,將李白諸多詩文系年。
有一段時間,學界很多人認為隻有宏觀的理論研究才有價值,把考証視為“雕虫小技”。郁先生反對這種“一刀切”的觀點,在他看來,乾嘉學派有過於煩瑣的缺點,但是其反對空談、崇尚實証的理念仍然值得被繼承與發揚。清人黃錫珪所著《李太白年譜》附錄了三篇文章,黃氏稱這三篇文章“的系李白真作,無可疑者”。郁先生發現,這三篇文章皆見於唐人孤獨及的文集《毗陵集》,於是對文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進行深入考証,最終斷定這三篇文章乃孤獨及所作。這種扎實的文獻考証,是宏觀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
20世紀50年代末上大學時,郁先生就經常去南京頤和路的南京圖書館古籍部看書,后來也常到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古籍收藏較多的圖書館訪書。1963年,他利用赴上海參與《辭海》修纂的機會,多次抽時間到上海圖書館抄書。前文已經提及,為編撰《唐刺史考》,郁先生不辭辛苦到處尋訪墓志文獻。在郁先生那裡,各種文獻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內在聯系的整體。正如孫望先生所說:“憑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辦法,但這只是賢皓同志資以考証的一個方面。此外,隨著問題性質的不同和資料情況的不同,他還採取多種途徑去求得疑難的解決:從詩文中去尋找內在關系,從歷史背景上去找外緣關系,或從時間、地點、官銜的異同上去找線索,或從親朋交游、離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時候從版本校勘上去尋求旁助,等等,途徑是多方面的。”
全面搜集文獻,充分挖掘新材料以及前人忽略的文獻,靈活運用文獻,使研究論証科學、充分、具有原創性,這也許就是郁先生在學術之路上能夠不斷突破的秘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