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勇,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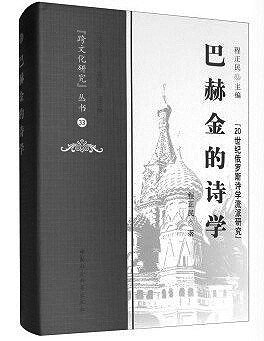


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三老”程正民(右)、童慶炳(中)、李壯鷹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合影。
【述往】
學人小傳
程正民(1937—2024),福建廈門人。1959年本科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留校在文藝理論組任教,講授文學概論課程。1965年調至蘇聯文學研究所,曾任蘇聯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蘇聯文學》雜志常務副主編。1993年調回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曾任中文系系主任。著有《20世紀俄蘇文論》《巴赫金的詩學》《俄羅斯文學新視角》等。
2月20日早上八點多,當程正民老師去世的消息突然傳來時,我一時驚得說不出話來。那天下午就有新學期的第一次課,我得有所准備,但備課期間不斷走神,有關程老師的點點滴滴蜂擁而來……
導讀巴赫金
我知道程老師的名字是1993年,但見到他本人已是1999年。那一年,我考進北京師范大學,在童慶炳老師門下攻讀博士學位。童老師打頭陣,給我們開設了《文心雕龍》專題課﹔程老師則緊隨其后,與另一位教授合開一門西方文論專題課。根據我的聽課筆記,程老師是2000年3月8日走上這門課的講台的。他告訴我們,他的課是讓大家細讀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他先講兩次,算是導讀,接著是大家的自選動作:選取某章內容,細讀一番,講解出來。
說實在話,巴赫金的這本書我雖早已買到(購書日期是1993年12月),卻一直躺在我的書架上睡大覺。隨著程老師的講述,隨著對話、庄諧體、狂歡化、復調小說、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等概念從他口中汩汩而出,我開始了對巴赫金的正式閱讀。因為頭一學期聽過童老師的課,我對兩位老師的講課風格忍不住要暗中比較。比較的結果是,如果說童老師主打慢條斯理,那麼程老師則主打“大弦嘈嘈如急雨”,這種機關槍般的語速讓我意識到,他不僅思維敏捷,而且還是個急性子。他要是唱歌,估計都會嫌“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節奏太慢,而是要換成“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的,為什麼呢?因為《喀秋莎》是四二拍啊。
這就是我對程老師的最初印象。這種聽覺效果,再加上那個精瘦、精干、精氣神十足的視覺形象,更讓我覺得程老師活力四射。實際上,那時他六十有三,已退休在家,卻被大他一歲的童老師拉入彼時剛剛申報成功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文藝學研究中心,成為退而不休的專職研究員,也成了童老師的左膀右臂。
話說2000年春天,我不僅細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全書,而且因為對第四章所論的“庄諧體”“梅尼普諷刺”“蘇格拉底對話”興趣頗濃,又決定把《拉伯雷研究》也讀起來,因為盡管前書也談到了狂歡式和狂歡化,卻仿佛是即興表演,我想弄清楚狂歡節、狂歡廣場、狂歡式的世界感受是怎麼回事,便無法在《拉伯雷研究》面前繞道而行,因為這本書中隱藏著這些問題的所有秘密。此書讀畢,我特意在書后寫了幾句,記錄彼時的激動之情,其中一句是:“讀此書期間,受到的沖擊與震動無與倫比。”也是在讀過這本書之后,我才終於寫出程老師這門課的課程論文《民間話語的開掘與放大——論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此文不僅受到程老師好評,而且發表也暢通無阻,甚至還獲得了《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優秀論文獎。現在想來,假如沒有程老師引導,我能順藤摸瓜摸到《拉伯雷研究》嗎?巴赫金能在我心目中佔據一個永久而重要的位置嗎?
也正是因為這本書,我才真正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書是讓你長知識的,有些書則是能深入你的靈魂的。於我而言,《拉伯雷研究》顯然屬於后者。
然而,直到程老師去世的那天,我才從書架上取下他那本《巴赫金的詩學》,開始了對它的真正閱讀。因為我相信,在一個人辭世之后閱讀其著作文章,才是對他最好的緬懷。因為這次閱讀,我才意識到程老師簡直就是文如其人:他的論述是質朴的,剛健的,冗繁削盡的,直來直去的,同時又是清晰的,謹嚴的,條分縷析的,舉重若輕的。經過他的清理、反思、提煉和歸納,巴赫金的整體詩學就既琳琅滿目,又井然有序了。這本書出版於2019年,是他晚年的著作。從字裡行間,我仿佛也領略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風貌,精神不僅為之一震。更讓我振奮的是,通過程老師的論述,我不僅復習了一遍巴赫金,而且還發現了巴赫金“藝術的內在社會性”與德國學者阿多諾“內在批評”之間的某種關聯,同時,把它寫成一篇論文的念頭也在我心中潛滋暗長。
論從史出
程老師在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曾經說過:“在20世紀俄羅斯各種詩學流派中,最重要的也最令我神往的是巴赫金的詩學。”(《我所走過的學術道路》)這話我信。在我的心目中,程老師雖然寫過《俄國作家創作心理研究》等書,自然是俄蘇文論研究專家,但這一專家的底色是巴赫金詩學。也就是說,假如沒有巴赫金這碗酒墊底,他的俄蘇文論研究是不是還能像現在這樣豐滿,或許就要打一個問號。
然而,直到程老師去世之后我才發現,他的巴赫金研究也正是起步於給我們這屆學生上課的世紀之交,因為那正是他發表《巴赫金的文化詩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的時候,也是鐘敬文先生鼓勵他將此文“擴展為一本書”的時候。於是才有了后來的《巴赫金的文化詩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又有了在這本書基礎上的拓展之作《巴赫金的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當我意識到程老師是在“最美不過夕陽紅”的季節才“咬定青山不放鬆”時,我對他的敬意又增加了幾分。對於許多學者來說,年屆花甲意味著收官階段的開始,程老師卻為自己設計了一個新的研究起點。如此志在千裡又如此壯心不已,怎能不讓人敬佩?
連童老師都佩服不已!記得2013年12月26日,文藝學研究中心像往年一樣,開了一個年終總結會。會開至最后,童老師說:“我們要扎扎實實做學問,要堅持學術本位。你看咱們的程老師,他就一直研究巴赫金,研究來研究去,就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所以,你們要像程老師那樣做學問。”
程老師的學問做得扎實,與他奉行“論從史出”有關,我就見他經常把這句話挂在嘴邊。比如,2014年7月上旬,中心在京郊大覺寺開務虛會,談及學科發展,童老師強調,以后的文學理論建設不應該再是大兵團作戰了,而是要每人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琢磨多年,然后再與項目結合。輪到程老師發言,他則指出:“如何處理理論、歷史和現狀的關系,我們需要認真考慮一下。論從史出很重要,但如果不重視現狀研究,也很難往前走。像別林斯基、巴赫金這種理論家,其實都是非常關注文學現實問題的。”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論從史出,史論結合”自然首先關聯著中國史學研究的傳統,但程老師之所以對此高度重視,並且要與現實相結合,顯然與巴赫金脫不開干系。在《巴赫金的詩學》中,我就讀到了這樣的論述:“從廣義上講,論從史出,任何理論問題必須回歸歷史,通過歷史研究闡明它的本質,闡明它的發展規律。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講,文學史是要尋找文學的發展規律的,但規律不是憑空編造的,規律是要從歷史的研究中得來的。”在另一處,程老師則直接指出:“巴赫金的文化詩學研究給我最大的啟示是不能把文學研究封閉於文本之中,研究文學不能脫離一個時代完整的文化語境,要把文學理論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隻有這樣做才能揭示文學創作的底蘊。”(《我所走過的學術道路》)這是從另一個角度對“論從史出”的強調。由此我也意識到,雖然在晚年,童老師和程老師都講文化詩學,雖然他們都強調“歷史文化語境”,但程老師所談論的文化詩學中多出了一個“論從史出”,這是來自巴赫金的饋贈。
由於程老師是巴赫金研究專家,遇到這方面的問題,我也時常向他請益。記得2012年,我曾問他巴赫金是否用過“對話性雜語”(dialogic heteroglossia)。因為那時我正帶著幾位學生翻譯美國學者布萊斯勒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其中的術語需要拿捏准確。2017年,我向他請教哪種《巴赫金傳》更值得一讀,因為彼時我正在琢磨錢鐘書的“暗思想”,想對錢鐘書和巴赫金進行比較。2022年正月,我去給程老師拜年,當面問他“詩學”在俄語語境中有哪些解釋,他馬上取出一本《文學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翻到第196頁,讓我看作者哈利澤夫的說法。他還說:“我那本《巴赫金的詩學》不是送你了嗎?我一開始就解釋了詩學的三層含義,你回去可以看看。”我唯唯。
從程老師家出來,我忍不住感嘆:程老師可真是一本活字典啊。與此同時,童老師的一個說法也在我耳邊響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天作之合
查記錄,童老師的這番話說在2009年3月11日。那天下午,中心成員開會,童老師說他准備卸任,要把中心主任交給李春青教授。談及中心的人員構成,他說:“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三老’‘五中’‘五青’。三老是我一位,程老師一位,李壯鷹老師一位。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們這個大家庭現有‘三老’,那就是如有三寶了?”
實際上,李老師那時才六十有四,稱“老”似不合適,真正的老人隻有童老師和程老師。他們都於1955年進入北師大中文系讀書,又都來自福建,也都在大學期間嶄露頭角,最終成為留校人選。所不同者在於,童老師當時在中文一班,程老師在中文四班﹔童老師提前一年畢業,程老師則是完成四年學業后正常畢業,二人遂由同學變為同事,同在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任教。后來,童老師雖也被抽調到學校教務處干過,卻基本上沒離開過中文系,而從1965年起,程老師轉入蘇聯文學研究所。直到1993年蘇聯文學研究所解散,程老師才重回中文系教書,在干過一屆系主任(1995年—1997年)后,他就退休了。
程老師能回中文系,童老師應該功不可沒。
據李春青教授回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程老師就成了童門弟子心目中的“副導師”,原因在於,那時候童老師已請程老師幫忙做課題、帶學生,等於是拉他入伙了(《我的“副導師”程正民先生》)。“蘇文所”解散后,程老師何去何從,本來是有些猶豫的,因為他也可以選擇去外語系,但童老師希望他“葉落歸根”。在童老師的支持下,程老師不僅回到了中文系,后來還被推到系主任的位置。
為什麼童老師要請程老師回來?答案其實並不復雜,我以為他是想找到一位得力的幫手。
話說20世紀90年代初期,童老師正准備厲兵秣馬,大干一番。但那個時候,文藝學教研室青壯年居多,他們雖然朝氣蓬勃,做學問是一把好手,但一旦進入行政管理、學科規劃層面,或許就顯得經驗不足。於是,尋找一位知根知底的知心朋友來為他出謀劃策、揚長避短,就顯得迫在眉睫。這樣,老同學程老師就成為最佳人選。因為他不僅謙和、低調、沉穩,而且腦子活,點子多,仿佛是“塔裡點燈,層層孔明諸閣亮”。
記得在慶祝程老師八十華誕的會議(“俄羅斯詩學發展新趨勢”學術研討會)上,羅鋼教授發言時把童、程二老師比作《紅樓夢》裡的釵黛關系,說他們是“兩峰對峙,雙水分流”。我則在致辭中借用蘇聯學者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中的說法,把童老師看作“主角”,把程老師視為“幫手”。我說:“在一個故事中,主角當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紅娘的幫助,張生就娶不到崔鶯鶯﹔沒有少劍波的參謀,楊子榮就打不進威虎山。可以說,在文藝學學科的建設中,正是他們這對老搭檔各就其位,各司其職,才完成了文藝學的學科敘事,把我們這個學科帶向了一個輝煌時期。”
紅娘是《西廂記》中的女二號,少劍波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參謀長,這兩出戲許多人耳熟能詳,是不需要解釋的,需要解釋的是普羅普的理論。在《民間故事形態學》中,普洛普歸納出七種角色——加害者、贈予者、幫助者、公主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假冒主人公——它們涵蓋了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圍繞著每一種角色又構成了一個“行動圈”,它們在故事中行使著不同的功能。在北師大文藝學書寫出來的故事中,童老師當然是絕對的主角(主人公),程老師則是完美的幫手(幫助者)。他們要尋找的“公主”則是北師大文藝學的“頂層設計”,或者是童老師所說的,尋找“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在這種尋找中,程老師一直心甘情願地當著幫手、配角、幕僚、綠葉,沒有絲毫怨言。這種角色意識不是走過場、做樣子,而是徹頭徹尾,心悅誠服,毫不含糊。
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裡,我親眼見証了童、程二人堪稱完美的合作過程。我甚至覺得,不用“天作之合”來形容,就不足以表達這種完美度。
紅泥小火爐
童老師去世之后,我開始擔任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記得“新官”上任之后,我第一次到程老師家中拜訪,他就講起了自己當系主任的往事:“當時是學校領導突然找我談話,然后就把我‘逼’上了系主任的位置。當了主任后,我去拜訪了系裡的幾位老先生。因為當時中文系矛盾多,情況復雜,我就跟鐘敬文先生、啟功先生訴苦,兩位老先生談笑間就給我出了主意、想了辦法。其實鐘老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像堂吉訶德﹔啟老則像哈姆雷特,他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世界就是由這兩類人組成的。這不是我的觀點,屠格涅夫早就寫過文章。當了主任就得干事情,干事情就要惹人,但隻要你是出於公心,又贏得了上面的支持,你就隻管干下去。”滔滔不絕,引經據典,簡明扼要,直指心窩,此謂程老師的談話風格。他在那裡現身說法,仿佛是手把手教我怎樣當主任。
2017年6月14日晚上九點多,程老師給我打來電話。他開口就說:“今天是童老師走了兩年的日子,真是快!我想他了,特意給你打個電話。”然后他又問我:“是不是會想到童老師,尤其是困難的時候?”我說:“是啊,因為我們既沒有童老師的智慧,更沒有他多年形成的那種威望。”於是程老師安慰我,說:“你也挺不容易的。以后遇事多商量,慢慢來,別著急。”實際上,我當主任期間,正是程老師意識到了我的“不容易”。雖然這些話顯得抽象、縹緲,但畢竟也是一種安慰,仿佛在“晚來天欲雪”的時節來了一個“紅泥小火爐”,讓我感受到了融融暖意。
2018年10月20日,文藝學研究中心主辦的“文藝學新問題與文論教學”學術研討會(第二屆)在京舉行,我請程老師致辭,他先是說了些面上的話,隨后就轉到我身上,說:“2011年在香山開會時趙勇剛買了輛新車,他開著車,把我和童老師送回了家。當時他是新手,車技一般,大家還不怎麼敢坐他的車。七年之后他已是一個老司機了,坐他的車妥妥的。”程老師說罷,下面便是一片笑聲和掌聲。
我知道這是他在為我鼓勁加油,於是立刻跟進一句:“謝謝程老師!”
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是在2002年。20多年之后,答辯委員會其他委員的臧否之詞大半都已忘卻,但程老師的一個說法我依然記憶猶新。他說:“趙勇這篇論文能拎起來,不像有些同學寫得比較散。他的論題是《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証法——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他提煉出了‘整合’與‘顛覆’這兩套話語,這就拎起來了。”
按我理解,“能拎起來”就意味著論文有了核心命意。那個命意就仿佛一個抓手,可以放開,四面出擊﹔能夠歸攏,萬取一收。“拎不起來”的論文不一定就寫得差,那裡面也有散金碎玉,只是還沒有煉成塊,塑成形。究其因,要麼可能是材料不過關,要麼就是方法有問題。我不敢說我的論文有多好,但好賴是有個抓手的﹔這個抓手是金鑲玉還是鐵家伙倒在其次。我能意識到這一點,全憑程老師的那次提醒,是他為我這篇論文的分量過了秤,命了名。他的說法盡管很朴素也很家常,沒有“填補了……空白”之類的贊詞,但我喜歡。后來,我之所以對一些諸如《薩特介入理論研究》《巴特結構主義思想研究》的博士論文有微詞,提意見,便是因為這些題目隻有論述范圍,沒有核心觀點。用程老師的話說,就是“沒有抓手,拎不起來”。若是用古文來說,最合意的句子應該是“無帥之兵,謂之烏合”。
盡管程老師的論文批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后來在許多年裡,我只是出了書奉上,請他雅正,並不敢隨便寫出什麼文章就讓他看。道理很簡單,一是他年事已高,二是他手頭的活兒也不少,我不能佔用他的有限精力和寶貴時間。
然而,也是從童老師去世之后,我又開始讓程老師審閱我的文章了。為什麼我要讓他受累?因為我在論文寫作之余,也常常寫一些涉及北師大人和事的文字,於是就有了讓程老師看看的念頭,因為他既可以指出寫法好壞,也可以鑒別事實真偽,甚至還可以給我提供一些細節材料。於是每每初稿既成,我便打印出來呈他審閱。通常三兩天之后,程老師的“評審意見”就能到位。當然,我敢頻繁打攪他,也是因為那些文字並非什麼高頭講章,可以讓他消愁破悶。尤其是后來得知程老師喜歡讀這路文章之后,我就更是沒有心理負擔了。
現在想來,這些年我不斷請程老師批作文、提意見,所圖者何?應該沒有什麼功利目的,甚至也不圖程老師的表揚。我大概覺得,每當寫到北師大中文系傳說中的人和事時,自己隻能從故紙堆中尋找資料,而程老師是現場目擊者,我需要請他把關、驗証,指點迷津。隻有這樣,我所回到的那個歷史語境——亦即他與童老師都反復強調的那個東西——才不至於太抽象、太骨感,而是有了那麼點血肉豐滿的味道。程老師也恰恰心懷慈悲,肚裡有料,於是他的評點常常恰到好處,他的建議往往切中肯綮。這種賜教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后來甚至覺得,隻有經他過目、被我再改之后,文章才拿得出手,否則,我心裡就不踏實。
每每想到再也不能向程老師請益,我以后隻能“文責自負”時,便不禁心中悲傷,有了一種“我有疑難可問誰”的荒涼。因此,對於許多人來說,程老師的離世,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師者、寬厚的長者,但於我而言,除此之外,還是一位熱心而嚴謹的文章把關人遠去了。
本版圖片由作者及程正民之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程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