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君莉,系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學人小傳
胡軍(1951—2022),生於上海,逝於北京。1977年考入哈爾濱師范大學政教系,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1991年獲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8年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曾任北京市哲學會會長、民進中央常委。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哲學研究,著有《金岳霖》《知識論引論》《哲學是什麼》《分析哲學在中國》《道與真》《知識論》《中國現代直覺論研究》《中國儒學史·現代卷》《燕園哲思錄》《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論知識創新》《究真求道:中國走進現代社會的哲學省察》等,發表論文近200篇。

胡軍著《道與真》

胡軍(右)與學者蒙培元在一起。

胡軍著《知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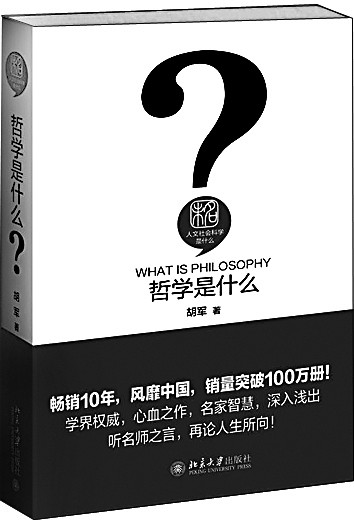
胡軍著《哲學是什麼》
【求索】
胡軍老師之於我,是如謎一般的人物。
他既懷有哲人的深沉幽思,又充盈藝術家的生命熱忱,從上海“棚戶區”到嫩江農場“馬棚”,從農場中學教師到北大知名教授,從文藝、體育愛好者到能與行家“過招”的准專業人士,他做真人、學真知、求慎思、踐真行,通過知識獲得生命的自由綻放,其學術人生可謂問道中西、立己達人。
從上海“棚戶區”到嫩江農場“馬棚”
胡軍老師出生在上海城隍廟東南角的一個棚戶區,那裡緊鄰著大上海最繁華的地段。在他的童年記憶中,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和狹窄幽暗的弄堂錯雜排列,五彩的霓虹燈和微弱的煤油燈交相映照,歡快激昂的迪斯科和夫妻吵架聲、孩子啼哭聲混合交織。談及那時的生活,胡老師常常感慨:“大多數人看見的是繁華,但真實的生活有很多艱辛和苦寒。”
胡老師兄弟姊妹五個,他排行老二。母親做外包工,每月賺三十多元錢,一家子就靠這點錢艱難度日。胡老師自幼向往獨立自主的生活,自言“比較欣賞一種孤獨、獨立的狀態”。1969年,胡老師的大姐已到崇明島農場下鄉,他本可以不去下鄉了,但18歲的他心想:“與其在家白口吃飯,不如到農村去,一來省了一口米,二來能有所磨煉。”他瞞著母親將戶口遷出,帶著母親的牽挂、帶著鄰友的不解,帶著一個裝滿書的大木箱,坐了三天三夜火車,遠赴千裡之外的黑龍江嫩江國營農場三分場。
農場的生活辛苦而充實。白天下田勞作,打谷、割麥,揮汗如雨,晚上五六十人同睡馬棚,聊天打牌,臭汗熏天。對胡老師來說,隻要能自立,這些艱辛都不算什麼,“我是一個自立的人,像我媽一樣,而且此后我有了更多自由”。待馬棚鼾聲四起,他以木箱為案,挑燈夜讀,凌晨入睡,日出起床。無論寒暑,胡老師“心有足樂,不知困乏”,心靜如水,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享受著書香帶來的愉悅。
勤勉讀書為胡老師創造了新機遇。1975年秋天,他被選到農場總部當中學政治教師。當時學校對政治課老師要求很高,新教師必須先積累講課經驗。他先講農業課,從馬鈴薯的種植歷史講到玉米的栽培方法,繼而再講各種農作物的習性,講得詳細而認真。一年后,胡老師終於踏上了政治課的講台。
從中學講台到北大課堂
到農場當政治老師后,胡老師仍然堅持刻苦讀書。一位同事送給他一本《邏輯學》教科書,是南開大學哲學系溫公頤先生編寫的,胡老師被深深吸引了,從此“與哲學結了緣,結了很深的緣”。
1977年恢復高考,初中畢業的胡老師憑著執著的追求、強烈的興趣,全力研讀母親從上海寄來的“青年自學叢書”。那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哈爾濱師范大學。其實,他的考分超過了不少著名高校的錄取分數線,隻因當時黑龍江省的政策規定,凡本省以中學老師身份參加高考的考生隻能就讀本省的師范院校,於是,胡老師告別了生活近十年的嫩江農場,到哈爾濱師范大學求學。
上大學前,胡老師從未接觸過英語,為了能跟上老師的教學進度,他開始近乎“瘋狂”地學習英語。有一段時間,他吃飯時聽英語廣播,走路時背英語單詞,隻要稍有空閑,就學習英語。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不懈努力,他的英語成績突飛猛進,不但在課堂上能跟上老師的進度,還參加了省裡的英語比賽,斬獲第七名。
在哈爾濱師范大學求學期間,胡老師的學識和為人都深受老師同學認可。畢業分配時,思想政治教育系的中國哲學教研室、西方哲學教研室、邏輯學教研室都爭著要留他,最終他選擇了中國哲學教研室,因為這個教研室的主任威望最高。天時地利人和,入職不久后,胡老師獲得了赴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的機會。進修期間,他得到樓宇烈先生親自指導,獲得儒雅溫和的湯一介先生的贈書,在張岱年先生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上深受啟發。
胡老師對當年北大哲學系的老師們印象很深刻,他不止一次說:“那些老師不僅博聞強識、脫口成章,而且學問做得非常好,老教授們對文本每個字的解讀都引經據典、細致入微,不得不讓人欽佩。”胡老師尤為敬仰張岱年先生對史料的熟練掌握、對哲學史概念深入精致的分析,談到張岱年先生時總是飽含深情,情緒激動:“當張先生邁著顫巍的步伐走進教室時,滿教室所有的中外學者全體起立,向這位學界泰斗鞠躬致禮,我因此受到了很大震動。我感覺到在北京大學這塊土地上,知識真的具有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
在北大進修一年半之后,胡老師重返哈爾濱師范大學,一向安分的他沒有過高的渴求,隻想穩穩當當教書,但不久有關部門下發文件,要求擬申報高級職稱的教師具有研究生學歷。經過努力備考,1985年胡老師順利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導師是湯一介先生。雖然胡老師考研總成績第一,但因為是在職委托培養的研究生,學校不給安排宿舍,他隻能租一間條件簡陋的小屋,寒窗苦讀。從未寫過學術論文的胡老師,苦讀三年后,以《金岳霖本體論哲學之分析》為題完成碩士答辯。張岱年先生評曰:“這篇論文我是從頭到尾全部看完的,文章寫得相當不錯。”憑胡老師的優異成績,原本可以直接推薦讀博,但性格剛強獨立的他選擇通過考試取得博士生入學資格。胡老師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是《金岳霖〈知識論〉研究》,幾位德高望重的答辯委員會委員給予很高評價,朱伯崑先生認為這篇論文代表著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在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基礎上,胡老師撰寫了《金岳霖》一書,此書獲得首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墨子刻專門給胡老師寫信,稱贊他的學問。
1991年博士畢業后,胡老師有留北大任教的機會,但為了遵守諾言,他依然返回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書。不過,北京大學哲學系一直求賢若渴,希望這位優秀畢業生回校任教。1997年秋天,一紙調令被送到哈爾濱師范大學,要把胡老師作為重點人才引進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他本人對此事竟毫不知情!次年,也就是博士畢業七年后,胡老師重返北大。
縱橫中西哲之間
在哈爾濱師范大學政教系和北京大學哲學系,胡老師都在中國哲學教研室工作,但因為研究金岳霖的緣故,他的研究路數更偏向於知識論和西方哲學,對西方哲學體系和研究方法頗有心得。胡老師經常說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些尷尬:“哲學界其他學科的老師比較認可我﹔在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看來,我卻是異類。”
在學術研究方法上,胡老師重視史料研究,認為史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但“更重要的是學者應該善於提出新的問題,做系統的結構性的理論思考與建構工作”。胡老師注重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他認為中國哲學重視古籍經典和經驗,而西方哲學注重邏輯論証。胡老師特立獨行的研究方法和獨特的理論常常使他遭遇反對意見,有時候處境難堪。胡老師詼諧幽默地稱自己的理論為“胡說”。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張永超教授總結:“胡老師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接續了馮友蘭、金岳霖以來的研究傳統,試圖回到問題自身做學理的探究。這是一種‘告別古今中西,回到問題自身’的思路。”
在古希臘眾多先哲中,胡老師最推崇亞裡士多德,特別欣賞亞裡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胡老師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以金岳霖研究為主體,他在研究過程中曾將金岳霖以及與其有關的著作反復閱讀了不下十遍,但對於金岳霖的一些觀點他並不認同,通過論文寫作與之展開對話:“比如我有這樣一個觀點,即金岳霖認為隻要感覺者的感覺是正常的,那麼他通過感覺所獲得關於外物的內容就是客觀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論証,即便是正常的感覺,得到的感覺內容也不是客觀的。在這個問題上,金岳霖還局限在一個很狹小的理論圈子內,他不知道與感覺認識相關的科學生理學方面的內容,我則能夠提供大量關於感覺生理機制研究的系統材料來証明金岳霖相關觀點的局限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周禮全先生是金岳霖先生的弟子,全程參與了胡老師的博士論文答辯。從個人情感上,對於胡老師對金岳霖先生知識論等相關觀點的尖銳批評,周禮全先生並不能接受也不能認同,但周先生認為胡老師的論文很有新意,分析深入到位。張岱年先生認為,胡老師的論文論証嚴密,敢於質疑權威,代表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趨向。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郁振華教授在《懷念胡軍教授》一文中寫道:“胡老師推崇金岳霖哲學,視之為中國哲學現代化之楷模,但不迷信。他對金岳霖哲學既有同情的了解,也展示了批判的鋒芒。比如,該書第四章《所與》對金先生的感覺論提出了尖銳批評。聚焦於感覺內容和外物的關系問題,胡老師考查了科學史和哲學史上的大量研究成果,進而質疑金先生的‘正覺論’和‘所與論’,拒斥其核心主張‘內容和對象在正覺的所與上合一’。馮契先生基本接受金先生感覺論的核心主張,胡老師曾撰文《“所與是客觀的呈現”說評析——以金岳霖、馮契為例》(2016),論文的基調跟前述第四章是一致的。胡老師的批評很犀利,很有分量,這樣的辯難深契哲學的本義。對於金(岳霖)—馮(契)學脈中人來說,如何回應胡老師的批評,是一個需要直面的挑戰。”
“對創新有著不懈追求”,這是學界對胡老師治學精神的一致評價。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說:“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循著‘接著講’或‘繼續講’的路子,比較關注的是傳統典籍的整理和經典的詮釋,做的是比較單純的中國哲學史工作。胡軍則試圖將自己的研究工作向內(理論創新)向外(社會關懷)兩方面拓展。”深圳大學人文學院王立新教授認為,胡老師的治學立足於知識創新,放眼未來發展,“胡軍教授是書痴,但不是書呆子。知識論和知識創新論,只是他的發力點,他的思想箭鏃,明顯是朝向未來發展的,這是他的致思目標”。
從胡老師對大學建設、學術發展的思考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研究知識論、倡導知識創新的現實意義。胡老師這樣解讀現代學術基本訓練:第一,以分科治學為前提的科學理論知識體系。比較明確的問題意識或研究對象是分科治學的前提。有了上述的問題或對象,我們才有可能對之進行精確嚴謹、系統精致的論証。此種過程性的或結構性的論証要依賴於某種周密而系統的思維方法理論。第二,在上述科學理論知識體系指導之下的可控的精確實驗。不得不承認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工業產品的生產基本就是上述兩個要素的無縫結合。胡老師認為,中國的高校應該在以上兩個方面取得突破,對於歷史悠久、地位獨特的北京大學來說,尤其應聚焦第一方面,即在分科治學前提下形成中國自己的科學知識理論體系。隻有朝這一方向努力,北大方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胡老師的學術道路與他對國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密不可分。因為豁達的性格,也因為特殊的人生經歷,在胡老師那裡,學術與人生、學術與生活是渾然一體的。他用生命去做學問,也用超出常人的熱心去服務社會。
胡老師曾任民進中央常委,還是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屆人大常委。在北京市人大履職期間,胡老師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多次起草文件、撰寫提案,為北大校園規劃多方奔走。清華大學胡偉希教授感言:“胡軍教授的貢獻遠遠不限於作為行業的學術界,他首先是一位熱心於社會服務的學者。他投身於各種社會服務以及社會公益活動,惠澤各界。”“這種社會服務意識,這種集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懷於一身的學術品格與學術意識,使胡軍教授的學術研究具有獨特的風格與鮮明的特色。”張永超教授談道:“胡老師關心水資源枯竭問題,關心現代社會的城市病,關心碳纖維的最新發展,關心網絡對現代人心的影響,對學界、教育界存在某種擔憂。我們希望老師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他常說‘我很困惑’。”
在最后一部文集《究真求道:中國走進現代社會的哲學省察》中,胡老師的家國情懷得到了充分體現,我們從中能夠讀出一位哲學工作者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深刻思考,也能讀出他對國家深沉的熱愛。
哲思中的詩意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胡老師不僅期許他的學生們有更豐富的學識,敢於挑戰權威,而且希望他們“能有高雅的情趣,進而有完整的人格和豐沛的生命力”。這與他自己的經歷密切相關。
談及自己的興趣愛好,胡老師的眉宇間常常會流露出自得和欣喜,那樣子簡直就像個孩子。他自言:“我年輕時就喜歡哲學、文學、詩歌、書法、唱歌、象棋、體育運動等。沒有家庭社區環境的熏陶,形成興趣純粹是因為自己曾經被這些東西深深地打動過。”
胡老師一生酷愛體育運動,小學時曾是全校跳繩比賽冠軍,還是全校廣播體操的領操員。他讀初二時被選拔進入校體操隊,苦練自由體操、跳馬、單雙杠、鞍馬、吊環等項目。中學長期的體操訓練,使得胡老師身體康健強壯,走起路來快步如風。在哈爾濱師范大學工作期間,胡老師與體育系的教師關系甚篤,常切磋交流籃球動作要領。任教北大哲學系期間,他倡導成立教師籃球隊,定期與系裡的學生比賽。胡老師生前在自家院子裡布置了一個籃球場,陽光燦爛時拍球、投籃,愉悅身心。
胡老師對書法的熱愛可以回溯到他的中學時代。有一次,胡老師被一幅書法作品所吸引,那些字結構、布局都極其到位,如行雲流水。從此之后,胡老師就開始苦練毛筆字。1969年赴黑龍江嫩江農場之前,胡老師所在居委會得知他寫得一手好字,便讓他在紅旗上寫“上海知青赴黑龍江嫩江農場三分場”,胡老師就是手持自己書寫的紅旗離開的上海。嫩江農場紅旗上的大字“上海青年赴黑龍江嫩江農場三分場”也是出自胡老師之手。農場偶有刮風下雨不能下田,胡老師偶得閑暇,不是看書就是練字。華東師范大學馬以鑫教授當時和胡老師同一個連隊,他回憶:“胡軍隻要有空閑,尤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是把白天搜尋到的各種舊報紙拿來寫毛筆字。胡軍的毛筆字一看就有很深造詣,帶有顏體風格,雍容大氣,似乎還有魏碑的端庄、嚴整。那時候,宿舍熄燈很早,我和他各自找到一盞用柴油的馬燈。往往是宿舍的兩頭,他在寫字、我在讀書,有時通宵達旦。”讓馬以鑫教授至今念念不忘的就是胡老師手抄的《浮士德》,“他是用藍色鋼筆抄寫的,版本應該比較老了,裡面還有很多繁體字”“在書籍極度匱乏的年代,胡軍居然有這麼一本手抄的《浮士德》”。
胡老師小時候,母親在織毛衣時偶爾會哼唱幾句越劇,他聽了覺得格調很特別,就逐漸喜歡上了,“它打動了我,打動我之后,我也就永遠放不下”。打動胡老師的,不隻有越劇,還有唱歌。在嫩江農場的日子,遠離家鄉,生活清苦,孤獨寂寞時,他便刻苦練習唱歌。經常用心琢磨在上海時買的《怎樣練習唱歌》。農閑時,在寬闊的農田裡,他放聲歌唱。過去,在擁擠逼仄的上海棚戶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下鄉生活賦予了胡老師一直渴望的自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常伴胡老師左右,友人戲稱他為“胡美聲”。2003年,胡老師跟隨宋慶齡基金會代表團一行赴台灣阿裡山交流,面對如詩如畫的風景,內心很是激動,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清唱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歌聲悠揚嘹亮,不少人以為他是專業歌唱家,到處打聽,才知道竟然是北京大學研究哲學的教授。
郁振華教授說:“我常常會想起面帶笑容、樂觀、幽默的胡老師,特別會想起他講演的場景:講著講著,他似乎覺得言述不敷用,於是便高歌一曲,響遏行雲,酣暢淋漓……”
除了唱歌,胡老師還迷戀吹笛,喜歡大提琴。年少時有一次偶然聽到笛聲,他就被深深打動了,后便自學吹笛,經常吹奏《小八路勇闖封鎖線》《我是一個兵》等曲目。在上海的弄堂裡,不少鄰居迷戀胡老師悠揚的笛聲。后來,黑龍江嫩江農場的上空也時常回蕩起他優美的笛聲,打動了不少知青。2013年年底,胡老師偶然聽到一位大提琴家演奏德沃夏克的《寂靜的森林》,如痴如醉,不能自已。他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如有來生,我一定自己買一把大提琴,如果沒有錢,借錢也要買一把,此后將終生伴隨著它,傾聽從琴盒內流淌出的美妙而動人的顫音。”胡老師看書、寫作、練字時常有音樂相伴,德沃夏克的《幽默曲》、舒曼的《夢幻曲》時常在他的書房中回蕩。
對於胡老師來說,哲學、藝術、體育都不是外在的知識或技能,而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養料。他在《生死相依:未知死、焉知生》一文中寫道:“生命的真正本質卻在於蘊藏在身體內的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是無限的、是超越時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胡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思想、人格、精神及其魅力是無限的、是超越時空的。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