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國賦,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卞孝萱(1924—2009),江蘇揚州人。中學畢業后在銀行工作,曾於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進修,業余自學文史。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民主建國會任職,業余仍從事文史研究。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1976年到揚州師范學院任教,1984年到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撰有《劉禹錫年譜》《元稹年譜》《唐代文史論叢》《劉禹錫叢考》《冬青書屋筆記》《唐傳奇新探》《唐人小說與政治》《鄭板橋叢考》等30余種著作,發表論文200余篇,主編《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等。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

卞孝萱(左)與南京大學教授程千帆在一起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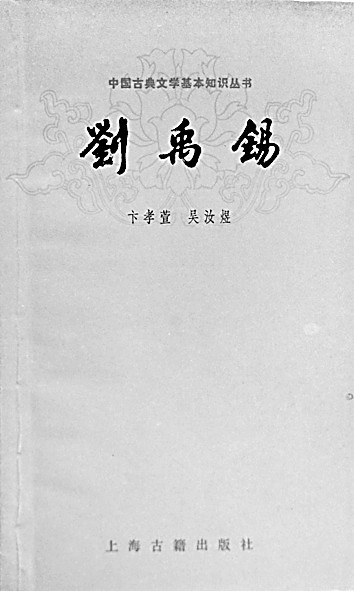
卞孝萱、吳汝煜著《劉禹錫》 作者供圖
【大家】
業師卞孝萱先生出身於揚州名門,因父親早逝而家道中落,生活清貧,靠自學成才。孝萱先生學術生命長達60年,著述超過一千萬字,在文史學界產生廣泛影響,著名學者程毅中先生評價:“卞先生績學多能,博聞強識,貫通文史,兼識書畫,著述豐繁,名馳中外。對唐代小說之新探,獨具慧眼,別出匠心,於學者啟迪尤多。”
孝萱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幾年了,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誕辰。我重讀先生的著作,結合自己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學習經歷,特撰此文,以表達對先生的思念。
專通結合 文史兼治
在卞先生豐富多樣的治學方法中,專通結合、文史兼治最為重要。這一方法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卞先生是揚州人,從小就深受揚州學派的影響。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介紹清代吳、皖兩大學派時認為:“(揚州學派)領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們研究的范圍,比較的廣博。”卞先生在一次訪談中說:“揚州學派兼顧訓詁與義理,不僅講究貫通群經,而且追求經學與諸子學及史學融會的做法,這對我以后的治學有很大的啟發。”(《“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7年第1期)他認為:“揚州學派區別‘陋儒之學’與‘通儒之學’。陋儒之學‘守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通儒之學‘實事求是,匯通前聖微言大義’(阮元《傳經圖記》)。焦循提出:‘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雕菰集·辨學》)他研究《易》,以數學和訓詁學為鑰匙,打開了前人未能打開的古籍之鎖。對鄉賢的治學方法(貫通、疏通、通核、通識、變通、匯通)和學術成就,我自少至老,銘記於心。”(《文史互証與唐傳奇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除揚州學派以外,當代學者對卞先生治學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卞先生受知於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協助范先生編撰《中國通史簡編》。范先生提出治學應做到“專、通、堅、虛”四字。所謂專,指學有專長,在某一研究領域深入挖掘﹔通,指會通、廣博﹔堅,指堅定目標,鍥而不舍,避免人雲亦雲﹔虛,指虛心治學,改正錯誤。卞先生所倡導並運用於科研實踐之中的文史結合、文史互証就是一種強調在“專”基礎上的“通”。強調專通結合,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學識修養。卞先生在《從〈唐代小說與政治〉說文史兼治》(《古典文學知識》1993年第5期)一文中對文史兼治的研究方法作了具體闡述,他說:“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結合,以史証文。這裡說的‘史’,主要指政治史和文化史。在佔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以小說寫作的政治背景為出發點,從傳奇作者的政治態度入手,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過表面的藻繪,進入了作者的心胸。”卞先生把文史兼治的方法比作庖丁解牛,他指出:“庖丁解牛,為什麼能做到游刃有余?就在於他肢解牛體時,能看准骨節之間的空隙下刀,刀刃運行於空隙之間,大有回旋的余地。我舉這個典故,是強調下刀的重要,即研究方法的重要。”
在卞先生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專通結合、文史兼治的研究方法運用相當普遍。以六朝史研究而言,他在正確看待六朝歷史地位的前提下,以廣泛利用文物考古資料、大力發掘文獻資料為基礎,力求宏觀、微觀兼備地研究六朝歷史,以彌補既往的不足,開拓今后的局面,建立起對六朝歷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體認識。關於利用新材料,他舉例說,六朝時期佔統治地位的門閥士族,為了固化其地位,在社會生活中高自標榜,相互通婚,不與寒人交往,六朝世家大族墓中發現的大量墓志所記述墓主的生平、婚宦情況往往証實了文獻記載的這一歷史現象。關於專通結合,他認為,六朝文化在外來文化(如佛教)與中土文化、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如道教)、士族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不斷發展,出現了儒、玄、佛、道、名、法各家爭鳴的局面,很多文人學士亦文亦史亦哲,理解這個時代的文化,非打通中土與異域的界限不可。(參見《關於六朝研究的幾點思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文史結合、以史証文也是卞先生從事唐代小說研究所採用的重要方法。以《唐傳奇新探》(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書為例,卞先生透過小說表面的藻繪,深入作者的心胸,所以《新探》一書不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具有不可忽視的史學價值。比如,對《河間傳》,前人都認為此傳有影射,但影射誰,意見分歧,卞先生根據大量史實記載考証為柳宗元告誡憲宗之作。他的論述既有嚴密的考証,也有對作品的感悟與分析,然后上升為理論的批評,既避免批評流於空洞,又避免使考據陷入煩瑣,體現出深厚的功力。
在《文史互証與唐傳奇研究》一文中,卞先生對以詩和小說証史的研究方法加以總結,提出要處理好個性與通性、古典與今典、表層與深層、實數與虛數、實境與虛境、明言與暗言、正言與反言、言內與言外這八個方面的問題,揭示出這一研究方法的深層次內涵,並使傳統的研究方法呈現出現代學術的新面貌。
因為做到了專通結合、文史兼治,卞先生的研究還呈現出點面結合、知人論世等特點。
協助范文瀾先生編撰《中國通史簡編》時,卞先生除了查找資料,還撰寫了其中部分內容,如此書第三編第七章第七節,內容涉及唐代史學、科學和藝術。這段工作經歷讓卞先生更加熟悉唐代文史,大約從這個時候(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他便以唐代文史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首先選擇一些重要的個案進行探討,以劉禹錫研究為例,卞先生出版了《劉禹錫年譜》《劉禹錫》《劉禹錫叢考》《劉禹錫研究》《劉禹錫評傳》等多種專著、合著,另發表多篇論文。劉禹錫的詩句“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卞先生常用以自勵,並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冬青書屋”,可見他對劉禹錫及相關研究情有獨鐘。對於李益、張籍、韓愈、元稹、王建、李紳、牛肅、南卓等唐代作家,卞先生同樣用力甚勤,撰寫《李益年譜稿》《張籍簡譜》《韓愈評傳》《元稹年譜》《關於王建的幾個問題》《李紳年譜》《〈紀聞〉作者牛肅考》《南卓考》等專著或論文。
卞先生重視唐代文學史上一個個重要個案的研究,但他並沒有將眼光停留在這些“點”上,而是力求做到點面結合,將個案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他關注作家的思想狀況、人生觀念、文學思想,關注與每一個作家關系密切的政治群體、文人群體,關注作家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態與文化思潮。卞先生憑借廣闊的學術視野,把個案放在整體之中進行考察,得出的結論客觀、全面、公允。
1989年5月,卞先生受聘擔任《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主編。編撰《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規模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卞先生主持編撰《隋唐五代文學分典》,歷時十二年,前后參加者百余人,選錄資料一千萬字,收錄作家約兩千人,引用古籍近兩千種。參與這項龐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可以說是卞先生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一次總結,也是他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由個案研究到整體研究、由“點”到“面”的一次成功的學術實踐。
卞先生在學術上的知人論世,可以韓愈研究為例。他注意到,韓愈在詩文中從不提及母親,李翱、皇甫湜所撰韓愈行狀、碑文中,也都沒有提到韓愈母親。卞先生從考察韓愈對其兄韓會為“宗兄”的稱呼入手,推斷韓會與韓愈非一母所生,韓愈乃庶出之幼子,進而推斷韓愈生母身份卑微,在韓父去世后,或改嫁或以乳母身份留在韓家,這樣韓愈自然不會在其詩文中提及母親。(參見《韓愈生母之謎》,《周口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這是一種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韓愈這段獨特的成長歷史,對其性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重視文獻 不尚空談
卞先生十分重視文獻資料,他在《淺談“專”與“通”》一文中指出:“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獻學的知識與手段,隻能是空談。”卞先生走上學術道路,正是從搜集、整理文獻資料開始的。
二十歲出頭時,卞先生在閱讀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當時汪兆鏞《碑傳集三編》尚未出版)以后,深深感受到由於戰亂,資料嚴重散佚,於是立志收集、整理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志銘、家傳、行狀等。當時,卞先生在銀行工作,去圖書館抄書、去書店訪求資料或訪問相關人物都隻能利用晚間和假日。經過不懈努力,他發現了一批包括袁世凱書信在內的珍貴文獻。多年之后,在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際,他先后出版了《辛亥人物碑傳集》(團結出版社1991年版)、《民國人物碑傳集》(團結出版社1995年版)。華中師大章開沅先生認為:“這兩部書的出版,是錢、繆、閔、汪之后的一大繼作,亦未嘗不可以視之為碑傳結集的余韻絕響。”
卞先生善於從類書、方志、檔案、佛經、道藏、碑傳、敦煌卷子等各類文獻中發現新材料開展研究,甚至從醫書中挖掘出了新材料。他從嘉慶《東台縣志》中發現鄭板橋《南梁曹貞女詩》,從《民國東台縣志稿》中發現鄭板橋《重修大悲庵碑記》,並對收在其中的佚詩、佚文進行考釋,從而撰寫《鄭板橋佚詩佚文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2期)﹔從醫書《重修政和經史証類備用本草》中找到柳宗元纂救三死方即《柳柳州救死三方》,結合相關文獻,使今人獲知柳宗元在永州的病情以及其與劉禹錫交流醫術之事實,由此考察柳、劉二人的友誼,探尋柳宗元被貶之后的心境。
卞先生重視並利用出土材料,曾撰寫《唐代揚州手工業與出土文物》(《文物》1977年第9期)﹔注重第一手資料和稀見文獻,撰寫《讀〈黃侃日記〉》(《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通過第一手資料《黃侃日記》,結合有關文獻,從律己、尊師、敬友、愛生四個方面,展現黃侃的學術風貌﹔卞先生發現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兩種劉禹錫詩集上有姚世鈺過錄的何焯批語,但在書庫中沉睡了二三百年,便把這些批語整理出來,在《唐研究》第2卷發表,為劉禹錫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卞先生重視收藏文獻並開展研究。前文提到,卞先生出版《辛亥人物碑傳集》和《民國人物碑傳集》,就是在個人收藏的基礎上撰寫成書的﹔在鄭板橋研究方面,卞先生家藏清代徐兆豐《風月談余錄》一書,其中有《板橋先生印冊》(即《四鳳樓印譜》),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鄭板橋集》所漏收。卞先生於1962年先后在《雨花》和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將此冊介紹給世人。后來他又為印冊作注,以印証史,訂正了前人關於板橋印章記載之訛誤。
記得1991年下半年,我在卞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他給我們上唐史研究課時,提到“《舊唐書》比《新唐書》好”。為什麼呢?卞先生在課堂上給我們做了解答,他認為:“《舊唐書》具有《新唐書》所不能代替的價值,所以從古至今,兩部唐書並行於世。《舊唐書》前半全用《唐實錄》《國史》。今天除篇幅很短的《順宗實錄》外,《唐實錄》《國史》已蕩然無存,故《舊唐書》前半史料價值甚高。后半雖無系統的實錄、國史可憑,但五代去唐未遠,文獻尚存,史官搜羅得大體完備,而且《舊唐書》不隨便改動文字,與《新唐書》好省字,好刪年代、數字、官爵等具體內容相比較,在保存史料這點上說,有其不可磨滅的作用。正因《舊唐書》具有保存史料原貌的優點,古今治唐史者無不以其為最基本的用書。”卞先生對兩部《唐書》編撰特點、文獻價值的比較,充分體現了他在文獻材料使用方面的嚴謹和卓識。
博採眾長 致力創新
卞先生自學成才,轉益多師,曾經求教於諸多學術觀點不同的前輩,因而形成了不囿門戶之見、不泥一家之言、博採眾長的學術理念。
范文瀾先生對卞先生的治學影響很深。卞先生寫過多篇文章,或回憶與范先生的交往,或總結范先生的學術思想。對於陳寅恪、柳詒徵、章士釗、呂思勉等學術前輩,卞先生也曾撰文對他們的學術方法、個性、學術貢獻與道德風范等加以總結。2006年,卞先生以82歲高齡在中華書局出版《現代國學大師學記》,通過豐富翔實的材料揭示章炳麟、章士釗、劉師培、黃侃、柳詒徵、陳垣、呂思勉、鄧之誠、陳寅恪、章鈺、盧弼、張舜徽等十二位國學大師的學術風貌與學術價值,為后輩治學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卞先生在此書前言中指出:“《學記》謹遵薪火相傳之義,旨在從國學大師的治學方法中吸取營養,重在繼承。對其不足之處,加以說明,使人理解。”
不囿陳說、力求創新、不願人雲亦雲是卞先生學術理念中重要特色之一,以他研究鑒真為例,先生曾說:“(關於鑒真研究)我沒有循人老路,而是另辟蹊徑,對鑒真冒死出國的歷史背景做深入探討,寫成《佛道之爭與鑒真東渡》一文。”(《“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訪談錄》)他在文章中指出,武則天崇佛抑道,佛教興盛一時,此時鑒真出家﹔玄宗為強調李唐正朔,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作為虔誠佛教徒的鑒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前往日本的。文章發表后,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關於鄭板橋研究也是如此,卞先生2003年在《鄭板橋叢考·后記》中指出:“有感於鄭板橋被人談濫了,我從1962年發表第一篇鄭板橋的文章起,就抱定宗旨:不寫沒有新材料、新論點的鄭板橋文章。”
關於以詩証史,今人多談及陳寅恪,實際上在此之前已有學者論及。卞先生在《現代國學大師學記·前言》中指出:“以唐詩証史言,清末劉師培已發表《讀全唐詩發微》,遠在寅恪經營《元白詩箋証稿》之前﹔以明遺民詩証史言,抗日戰爭期間鄧之誠已經營《清詩紀事初編》,亦在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之前。學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師培,忽視之誠,誤矣。《學記》榷論三人以詩証史,庶幾無偏。”因此,卞先生在《現代國學大師學記》中專門撰寫《劉師培以唐詩証史》《鄧之誠與〈清詩紀事初編〉》二文加以論述。
卞先生治學不囿陳說、致力創新的特點在他的唐傳奇研究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南京大學有關唐人小說的研究已經形成一種學術傳統,汪辟疆先生編著《唐人小說》、程千帆先生出版《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和卞先生同輩的周勛初先生著有《唐語林校証》,主編《唐人軼事匯編》,並出版《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等專著。孝萱先生的治學方向,五十歲以前偏重於唐詩,五十歲以后偏重於唐傳奇,尤其是先生1984年調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以后,在唐傳奇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就斐然,先后出版《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唐傳奇新探》(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小說與政治》(鷺江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卞先生在《從〈唐代小說與政治〉說文史兼治》一文中指出:“我認為,做學問最忌隨波逐流,人雲亦雲。我試圖另辟蹊徑,走一條前人沒有涉足的新路子,即從小說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來對唐傳奇進行剖析。”多年來,卞先生著眼於唐代小說與政治關系的分析,對唐人小說提出很多新見。
卞先生晚年把研究領域拓展到傳統書院。書院對中國傳統的教育、文化、學術、道德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書院歷史應該得到充分關注。他在《南京曉庄學院學報》主持《書院研究》專欄,還與人合編《書院與文化傳承》(中華書局2009年版)一書。這些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鑒於學界研究家譜的文章相對較少,很多家譜中的資料尚未得到充分發掘,卞先生在《淮陰師范學院學報》主持《家譜研究》專欄,關注家譜研究,並撰寫《家譜中的名人身影——家譜叢考》(遼海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體現出鍥而不舍的學術創新意識。
卞先生在研究中注重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在《國學之內涵、價值及當代意義》(《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他稱頌章炳麟、黃侃、柳詒徵、呂思勉、陳垣、鄧之誠六位先生“所表現的擔當道義的大丈夫精神,是國學的閃光,民族的驕傲”。他指出:“‘國學熱’適應了民族本土文化復興的時代潮流。要從時代、國家和民族的高度,傳承發展國學的精華,激活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賦予其時代價值和當代意義。尊崇國學,絕不意味著自我封閉,而是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並在研究國學的同時,吸收、融合東西方優秀文化,與時俱進,使國學精神與時代要求相適應。”卞先生在《現代國學大師學記·前言》中說,編撰此書的出發點之一就在於“不僅揭示大師們的學術業績,並表彰其愛國情操”。
提攜后學 明燈指路
卞先生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十分注重文史、藝術等學科的人才培養,提攜后學。他在談到成立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推進六朝歷史文化的學術研究時指出:“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著力培養新人,使學會保持較強勁的學術活力。”(《“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訪談錄》)其實不僅是在六朝史研究領域,卞先生對於文史、藝術等領域的學科建設、中青年人才培養都相當重視。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編纂的論文集《薪火集》匯集了幾代教師的學術研究成果,卞先生為之撰寫序言,加以褒獎。他還曾為幾十位中青年學者的個人著作作序或撰寫評論文字進行推介。
1991年,我剛入卞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對唐人傳奇很感興趣,在卞先生指導下確定了博士論文選題《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卞先生十分重視學術規范,強調要重視海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注重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尋求突破。在卞先生指導下,我對前人研究唐傳奇的情況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先后撰寫《〈古鏡記〉研究綜述》《〈鶯鶯傳〉研究綜述》《〈李娃傳〉研究綜述》等文章。在課堂上,卞先生希望學生們要有開闊的學術視野,注重文史兼治,這些學術思路都來源於他自身的實踐,為我撰寫博士論文提供了很多方法論上的啟迪。我畢業以后,編撰《隋唐五代小說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初稿完成后,寄給卞先生,八十歲高齡的孝萱師認真審閱書稿,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並寄贈台灣藏《善本序跋集錄》所收4條明清文獻,為拙著增色許多。
孝萱先生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思想,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其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好學不輟,老而彌堅。卞先生以自己的生命歷程闡釋了“活到老,學到老”的人生哲學和不懈的學術追求。2009年7月末,也就是去世前一個多月,卞先生還在手訂《沒有錢穆名字的錢穆家譜——〈錢氏宗譜〉資料的發掘利用》,此文發表於《中國文化》2009年第2期(與博士生聯合署名)。如今,先生雖已駕鶴西歸,但他的學術精神如一盞指路明燈,時時陪伴著我們在學術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