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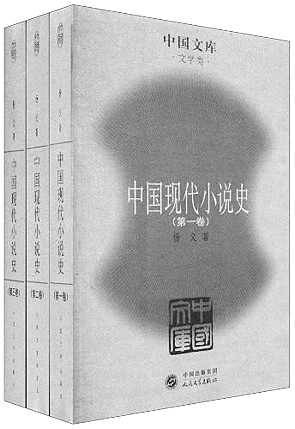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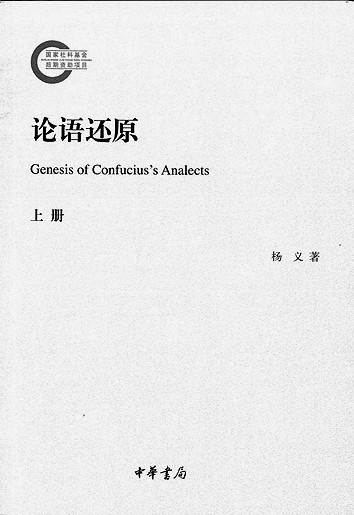
作者供圖

楊義(右二)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同事在一起,左一為本文作者。作者供圖
【大家】
學人小傳
楊義(1946—2023),廣東電白人。文學史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970年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1年碩士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曾兼任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文學評論》主編。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敘事學》《文學地理學會通》《論語還原》等。
楊義老師去世已經幾個月了,這段時間我協助師母處理他的手稿、圖書的捐贈事宜,60多部個人著作,成箱的手稿、筆記、卡片,還有幾部正在編輯出版流程中的書籍,研究范圍從文學史到敘事理論,從圖志學到文化詩學,從文學地理學到先秦諸子學……很難想象這是一位學者能夠獨自完成的工作。想及此處,心中涌起沉甸甸的思念和感佩。我有幸和老師接觸較多,他對我的教導深入我人生的方方面面,歷數不盡﹔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如果你的研究沒有政治抱負,你的學問做不大。”
他所說的“政治抱負”,不是指個人職位的高低,而是強調知識分子所肩負的文化使命,倡導知識分子堅守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參照西方的現代經驗,激發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力,提煉其中的中國智慧。
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化、現代學術的政治屬性是一個重要話題,從章炳麟、王國維、梁啟超等人起,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轉型中就包含著強烈的政治訴求和民族意識,其所遵循的思路,無非是此后魯迅所總結的“外之既不后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中國現代學術正是在此張力中展開,一方面我們努力以開放的心態去學習一切西方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另一方面我們在傳統的血脈中堅守我們的夢想與希冀,對這個古老文明體的未來抱有樂觀的信念,期待中華文明更富生機,呈現“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晚清民國以降,歷代學人人生境遇不同,知識結構各異,但無不堅持此思路,使得中國現代學術在歷史的激流中有所堅守和拓展。尤其是楊義這代於20世紀40年代前后出生的學者,在新中國接受了較為完整的教育,經歷了特殊年代的動蕩,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新時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契機,他們對傳統有著近乎鄉愁般的溫情,而新文化的立場又賦予了他們評述的分寸,改革開放大大拓展了他們的視域,也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緊迫感。這批學者的研究別開生面,深度、廣度不輸於前賢,其開拓性成果對后來的學術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
在自傳性散文《浮生回想錄》中,楊義說自己是廣東電白小鄉村一戶貧民家庭的孩子,從小就放牛,自己的文化啟蒙,大概就是聽讀過幾天私塾的父親在勞作之余用古腔古調吟誦唐宋詩詞。文化的魅力讓這個少年著迷,多年后,在接受央視《大家》欄目採訪時,他還用電白的方音模仿自己父親當年吟誦“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的場景。他還在文章中親切地稱古典文學名篇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約定俗成的教科書”“長效的民族素質的滋養劑”。
新中國成立后,村中來了老師,這個在水塘邊放牛的孩子有了進學堂的機會,那種一刻千金的緊迫感始終牢牢地抓著他。他深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所以要逢考必勝,把一本本教科書翻得稀爛,近乎倒背如流。此后,他成為當地第一個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之后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了當時人人羨慕的北京石化總廠宣傳部門工作。再往后就是一段動蕩的歲月。那些年,他保持著內心的定力,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單位圖書館封存的書籍,認真讀了《資本論》《魯迅全集》等大部頭著作,寫下了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他后來說:“人生一定要讀幾本大書,不一定都能讀懂,但能夠借此去了解偉人思考問題的方式”。
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復,楊義心中的文學夢想再度萌動,他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和王士菁兩位先生,成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屆研究生。唐弢對這個學生嚴厲有加,他注意到了楊義的敏銳,善於發現問題,善於獨辟蹊徑,能夠洋洋洒洒地寫文章,身上有一股壓制不住的才子氣﹔但作為一個同樣有著才子氣的人,唐弢對此有著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才華可以成就人,也可能讓人失之輕浮,而輕浮是治學的大忌。當楊義的碩士論文《魯迅小說綜論》完成時,他展現出來的學術潛力足以讓兩位導師滿意。在留所工作的問題上,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魯迅研究室主任的王士菁甚至提出:“如果不留這個學生,其他人我一個都不要。”留在文學所是一段學術傳奇的開始。很快,這個新人完成的工作便令整個學界甚至他的導師刮目相看。
留所之初,楊義便提出要獨力寫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那個集體著史之風尚存的年代,這樣的計劃近乎狂妄。他的導師唐弢,正是新中國最具影響的一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編,只是特定年代,牽掣甚多,這套文學史雖確立了該學科著史的規范,但在寫法和體量上卻未能依照唐弢本人的心願,留下了永久的遺憾。作為一個對現代文學發展歷程如數家珍的學者,唐弢有著別人無可比擬的優勢,所謂“重回歷史現場”的難題,對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他所倡導的社團流派的研究思路更是成為此后文學史研究最具活力的資源。楊義正是從自己導師的最強項起步的。如何像導師那樣對現代文學的背景了如指掌?唐弢給出了路徑:看期刊,看原版書。楊義每周拿一個布包,從文學所圖書館背回厚厚一摞民國期刊和圖書,看完一包還回去,再借一包,周而復始,十年不斷,兩千多種原版書、上百本期刊合訂本,在那個布兜中,也在那個青年人的頭腦中輪轉了一遍。文學所當時有著高校不可比擬的優勢,鄭振鐸、何其芳、錢鐘書等人籌建的圖書館藏書極其豐富,對民國書刊的收集更是不遺余力﹔資料室的圖書剪報工作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在網絡資源尚未出現的時候,為學者提供了一個“手工版”的論文數據庫。最好的研究儲備就擺在那裡,等待願意真正為學術奉獻一生的人前去開掘。不僅楊義自己,他的家庭都為此轉入了一種特殊的節奏。20世紀80年代,人們大都處於蝸居狀態,楊家也是如此。妻子張環為了不打擾楊義寫作,總是給他准備好幾天的飯菜,就帶著孩子回娘家去住。如今很多同輩學者回憶起來,還在感慨:楊義在家中能夠享受到不問柴米、心無旁騖的“待遇”,我們怎麼和他去比。
寫一部小說史為什麼要下這麼大的功夫?這不僅是當時學術界朝氣蓬勃的風氣使然,也源於海外漢學界成果的激發。美籍學者夏志清的著作對中國學者觸動極大,他對一系列作家精彩的評述、討論現代文學發展進程時運用嫻熟的西方文學參照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但夏志清有他無法克服的局限,他關注的是若干個“點”,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的熟悉程度,遠不及唐弢等人。想要超越夏志清,超越海外漢學的成果,不僅要更新研究方法,更需要展現出一種研究體量上的碾壓性優勢,要真正把這個學科的家底摸清楚,靠大數據出新思路,從而贏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無可爭議的主導權。楊義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工作。捎帶應該提及的,這是唐弢留給這個專業的遺產,也是楊義這一代學者共同的著力點。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正是沿此思路狂飆突進:一方面,馬良春、徐迺翔、張大明等人組織的大型資料整理工程全面鋪開,為學科奠定了初步的文獻基礎﹔另一方面,社團流派的研究思路被諸多學者所採納,南社、京海派、鴛鴦蝴蝶派……很多此前的學術禁區成為新時期現代文學研究再出發的生長點。楊義是其中最具雄心的一位,他不滿足於某個具體的領域,而是想完成一種通盤的考察,既承續自己導師的心願,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建立一種更為宏闊而周密的敘事。這是學術的政治,也是學術的智慧,我們無意和海外漢學界爭短長,我們是在他們的啟發下,充分激活自己的優勢,從而將中華文化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層級。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寫作小說史的十年確立了楊義的學界地位。當第一卷厚達一尺的書稿擺在當年還是青年編輯的李昕案頭時,這位對新時期文學史再版工作下足了苦功的編輯一眼就看出此書的價值。正是在李昕的全力支持下,這個默默無聞的學者撰寫的這部開創性著作破天荒地成為高校文科教材。唐弢在為該書所寫的評論中,有一句話讓人感慨萬千,他說:“我不喜歡楊義的才子氣,卻佩服他的硬功夫。”當才華和努力集中於一個人的身上時,當他能夠擺脫自己導師輩所受的時代束縛、任意揮洒時,當他有幸身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能夠充分利用幾代人積累的學術資源時,一位真正的學術大家有可能產生,這是個人的幸運與機遇,也是新中國學術在艱難積累后的爆發。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戲稱,文學所的一個青年人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地下工程”。小說史的影響迅速傳到了海外,蘇聯科學院院士費德林說,楊義自己就完成了一個研究所的工作量,夏志清更是對這位學生輩的研究者稱贊有加,慷慨地稱其為新一輩“治小說史文學史之第一人”。
二
小說史的成功讓楊義肩負起了更大的學術責任。數年后,楊義擔任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在現代文學領域,他和張中良、中井政喜一起,充分借助對期刊書籍的精熟,寫作了《中國新文學圖志》,讓圖像以最具啟發性、最為活色生香的方式,進入了研究者的視域之中。文學所首任所長鄭振鐸開創的插圖本文學史的研究傳統,在楊義這裡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圖像不再是配角,不僅是証據,而且是一種語言,“以圖出史、圖文互動”,圖像本身的敘事性、人文趣味,都成為研究者靈感的源泉,也使得文學研究成果真正走向了民眾。蕭乾先生說,這是曠世奇書,讀來如入寶山,琳琅滿目。
但楊義更大的興趣還在令他從小魂牽夢繞的古典文學。150萬字的現代小說史完稿后,楊義將自己的學術觸角伸向了古代小說,一本《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成為他投身古代文學研究的開端。相對於領域的拓展,理論建構能力更是楊義的長項。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理論盛行的時期,從西方引入的文本研究的技巧,極大地彌補了以往社會文化批評的不足,讓研究者能夠真正深入文本的內裡,推敲文字背后的意圖,使得人文研究更具技術層面的精密性。在充分考察了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敘事作品后,楊義敏銳地意識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深刻地反映在敘事的經驗和技巧中,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理論總結。廣博的古典文獻閱讀,更使得他深感用西方敘事學理論來套中國文學作品時有“帽小頭大”的局限。借助對方的啟發,對中國古代傳奇故事講述方法進行系統總結,這是我們回饋世界最好的方式,也是真正賦予敘事理論以世界性的必要途徑,而具體做法正如他自己設定的,“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參照西方現代理論,貫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創造新的學理”。1997年出版的《中國敘事學》一書正是此思路的展現。從文學史研究到理論創新,楊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小說戲曲並非中國古典文學的主流,詩文才是,楊義的研究重心很快便轉向了古典詩學的領域,《楚辭詩學》《李杜詩學》等作品陸續寫定。在這些著作中,楊義嘗試著提煉中國文學自己的概念范疇,如用“醉態思維”去替代以往研究給李白貼上的“浪漫主義”標簽,借助“巫風楚語”去理解屈原作品的瑰麗雄奇之美……楊義在找尋閱讀古典詩詞更為貼切的方式,以破解詩騷傳統和唐宋詩詞沉澱於中國人文化基因中的密碼,並將其視為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基礎。和大多數古典文學研究者不同的是,楊義更為開放地採用了一系列現代文藝方法去深入文本,對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會心”處更為看重。他為屈原等作者的實際存在進行辯護,對古代文獻的辨析採取了更為尊重實存的方式,這使得他拉開了與疑古學派的距離,也為此后的一系列“還原”研究埋下了伏筆。兩部詩學研究著作之后,捎帶著,一本對於中國詩學特質的總結之作《感悟通論》完成了。從具體的研究對象起步,以涉及文獻的體量和獨特的解讀方式取勝,最后以理論思考作結,楊義的研究在不斷變換著領域,但有始有終,從容不迫,正如他的好友李昕所說,“每挖一個坑都能打出一口深井”。
對李杜和屈原的研究,讓楊義開始著力思考中國文學的地域問題和民族問題﹔兩所所長的任職,也要求他打開視野,充分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貢獻。這是他學術體系的一次重要調試:在文學發展的時間坐標上,又增加了一個地域空間的坐標,使得每種文學現象都有了自己的“年齡”與“籍貫”﹔同時,不再將少數民族文學視為一種邊緣的存在,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充滿活力的文學樣態,在與漢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形態。上述工作使得他對於中華文明的特質和意義有了更為深切的理解。在歷史長河中反復碰撞激發而成的文化認同,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力量。正是循此思路,楊義明確地提出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構想:“我本人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是對漢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繪制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文學地理學會通》等書承載了他的理論思考,《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則提供了操作演示,其旨要正如他自己所總結的,在大文學觀的統攝下,充分關注中國文學的時空結構、發展動力體系和文化精神深度,拓展與之相關的民族學、地理學、圖志學和文化學四大領域,從而讓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解讀與其歷史進程更為貼近,讓中國文學呈現出來的面容更為細致可人。
文化地圖的重繪,是中國學界研究思路的一次飛躍:對內,展現了我們對不同文化現象的重新評估﹔對外,顯示了我們對於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充分肯定。這是在更大的范圍內摸清家底,為中國文化重辦一張“身份証”,以便他更為從容自信地交游於“世界文化沙龍”。應該注意到,對於地域空間和民族文化等問題的重視,同樣是西方學界的著力點,借此超越國別文學的局限,更加凸顯文化的多元性與豐富性。我們建立中國學術自己的話語體系,又保持著最大限度的和西方文明的貫通性。學術是為了交流,讓別人聽得懂、樂意聽,能夠從中真正理解中國的智慧,這是民族化和世界化的辯証統一,也是研究領域“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體現。在楊義這代研究者的身上,那種治學的飢餓感,那種出色的消化西方學術思路的能力和充分運用共和國大型資料建設成果所帶來的底氣,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立帶來了破局的契機。
三
再往后,楊義當選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並在卸任所長職務后,南赴澳門大學兼任講座教授。楊義是廣東人,粵語鄉音,嶺南青翠,更喚起了他當年投身中國文學研究的初心。時任澳大校長的趙偉教授提出“一流的大學應該有一流的本國語文專業”,也為楊義的學術拓展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空間。在澳大朱壽桐教授等同人的關照下,他可以將全部的時間精力投入研究工作之中,多年的治學經驗提示他,自己的學術必須再往前一步,進入一個更為前沿且可能更具爭議性的領域,即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對先秦諸子進行本質上和生命上的還原研究。
“還原”不同於“疑古”,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重在梳理后世文獻的累積過程,找尋古史最初的模樣,為歷史做減法﹔“還原”其實更類似於西方聖經學的研究方式,考察一部經典的生成過程,辨析其中的意義增值。以《論語還原》一書為例,楊義關注的重點是從篇章學的角度分析參與編纂《論語》的孔子弟子們的權力分配、競爭、卡位和妥協情況,以此梳理《論語》的成書過程,將其作為理解儒家思想的契機﹔對不入該書的其他孔子文獻,也不簡單地判定為偽作,而是將其視為不同視野、不同記憶中的孔子的面相——判其真偽的果決,讓位於考其原委的小心,而在此過程中,對於先秦兩漢簡帛傳抄書籍制度造成的文獻差異持有更為寬容的態度,對於基於民族志的資料和文化地理學視野中的口傳資料的真實性抱有更充分的信心。從2011年年底直到去世,楊義的成果量令人極度驚訝。赴澳大的第一年,《老子還原》《庄子還原》《墨子還原》和《韓非子還原》四書同時出版,此后,《屈子楚辭還原》《論語還原》《兵家還原》以及重新返回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魯迅血脈還原》等著作先后完成。新的研究領域自然會有更多對既有規范的打破,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過程也很難保証每一個論斷都立得住,評價留給歷史。讓人肅然起敬的首先是過程,一位學者居然建構起了如此宏大且雄心勃勃的學術體系,他不斷地突破著既有的學術格局,也不斷突破著自己的研究極限。早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時,他在和夏志清的通信中便提到了一個已然驚人的學術規劃:在做完古典小說研究之后,再去研讀我國古代之文史詩詞。夏志清則勉勵他要做一代“通人”。當一路從文學地理學研究、先秦諸子學研究走過,回望當年40歲出頭、意氣風發的自己時,他為自己的學術規劃做的也是“加法”。自然,不是沒有代價——消耗自己以滋養學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兩句,如今讀來,分外感喟。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楊義及其同時代的學者,對文化傳統懷有溫情,對世界文明秉持兼收並蓄的開放心態,借助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發展契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作出了切實貢獻,他們的學術實踐為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為推動“第二個結合”提供了重要啟示。
全面評價楊義的學術成就,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沉澱。他建立了一個極為宏闊的治學體系,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所言,這是一個著眼於古今文學的貫通、中外文學的匯通和中華文學的融通的大工程。但我們要注意到,其中有一條貫通的主線,即他的研究始終有明晰的政治抱負:要摸清中國現代文學的家底,要建立中國文學自己的敘事理論,要用圖志學建構中國特色的圖像研究體系,要錘煉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范疇,要為中國文化發一張個性鮮明的“身份証”,要繪制一張縱橫開闊的中國文學地圖,要為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增加地理空間的坐標,要還原諸子、探究中華文明的本源……所有這一切,都著眼於“國之大者”。尋找並維護大國學術風范,一直是楊義以及他這一代學者共同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