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復,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學人小傳
葉舒憲,1954年生於北京。現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榮譽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著作有《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等60余部,譯著7種,論文數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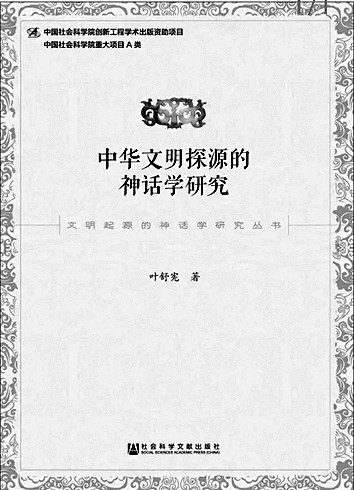
葉舒憲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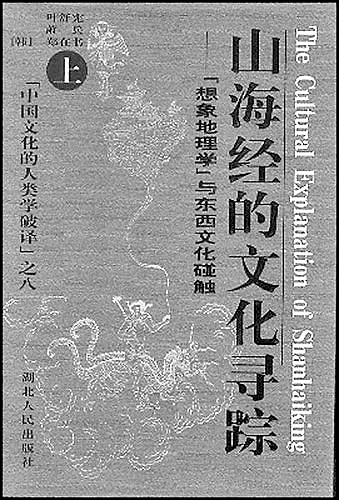
葉舒憲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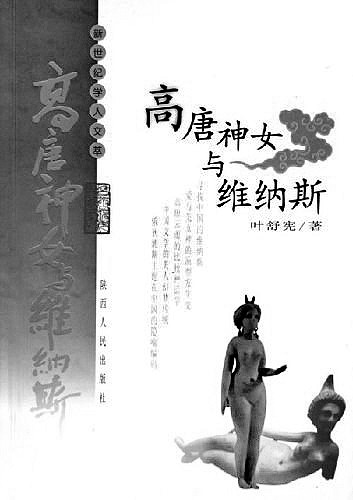
葉舒憲的著作

葉舒憲(左)在田野考察
【求索】
葉舒憲教授1987年主編、主譯論文集《神話——原型批評》,1992年又出版專著《中國神話哲學》,至今數十年間,他已出版了60余部學術著作(含合著),發表了數百篇論文,還翻譯、主編了多種著作,可謂著作等身,學殖強健。這是長期付出巨大心力、辛勤勞動的結果,其中甘苦,大約隻有浸淫於學問中人才得體會一二。
葉舒憲是一位視野寬廣、思維敏捷、勤奮篤行的學者。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於其所長期從事的關於中國神話的人類學神話原型批評,他所創獲的學術成果,在當今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評述、概括王國維學術研究特色時說,觀堂先生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証”“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百年以來,我國人文學科的代代學人,踵學術前賢而受濡染者多矣,葉舒憲是其中習得的一位。
神話:
文化的編碼和基因
葉舒憲教授關於中國神話的原型批評,始啟於榮格與弗萊的原型批評學說,卻並未拘泥於此,亦步亦趨。榮格與弗萊的“原型”說,一般地局限於精神分析的“集體無意識”論與文學溯源的視野范圍。前者稱,原型作為“種族記憶”,是神秘的“集體無意識”﹔后者以為,神話作為一切文學的“原型”,是“反復出現的原始意象”,雲雲。葉舒憲以為,這兩者都是頗有局限性的學術理念,在對榮格、弗萊原型說有所接受而批判的前提下,可以爭取在學理與方法論上有所突破。
葉舒憲說,“我在20多年前(引者按:約指20世紀80年代中葉)翻譯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時,基本上延續的是文學性的神話研究路徑”“近十年來,希望把神話從文學本位解放(或者稱釋放——原注)出來,作為文化的編碼和基因來看待”。他談到,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深受艾利亞德的啟發,不過他還隻在文學范圍談原型,局限性明顯”。他意識到,“神話是文、史、哲、藝術、宗教、心理、政治、教育、法律等的共同根源”“人類學的‘文化文本’概念,足以打通以往相互隔絕的學科關系。像文學文本、藝術文本、歷史文本等等,統統可以視為文化文本的某種形態,處於同樣有待於詮釋和解讀的召喚狀態”(廖明君、葉舒憲訪談《迎接神話學的范式變革》)。這裡所言,從關於神話原型的文學理念,到將神話原型批評釋放於文化研究這一范疇領域,便是葉舒憲所認知與踐行的“人類學轉向”。
這就不難理解,譬如關於《山海經》,為什麼魯迅先生稱為“古之巫書”(《中國小說史略》),而葉舒憲將其改稱為人類學意義的“神話政治地理”了。魯迅“古之巫書”這一學術結論,雖然寫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但實際已經是一個人類學意義的學術判斷。葉舒憲將《山海經》看作“神話政治”之作,証明他所接受的人類學神話觀,是西方人類學界一貫頗為流行的神話學大概念。這是因為,他將《山海經》這樣有關靈玉的巫文化,也歸類於“神話”范疇之內,不妨稱為“廣義神話”說。的確,西方關於神話的文化人類學,一般將原始神話、圖騰與巫術等,都劃歸於這一神話學大概念之下。葉舒憲斷言,“全世界幾乎所有文明都是由神話編碼的”,這是將弗萊關於“神話”為一切文學的“原型”理念,改造為人類一切文明的“原型”即神話。葉舒憲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中國所有傳世典籍中,沒有任何一部書能夠跟《山海經》平起平坐”。《山海經》所載錄的眾多神山的“神話”中,“有140多處產玉,沒有一部可以比之”,而以往學界“把神話文學化”“隻研究類似童話故事的東西”,在他看來,“這是研究中國文化最大的誤區”。他要求“把過去文學化的‘中國神話’這個概念,反過來叫‘神話中國’”(《“〈山海經〉雖極難懂卻獨家保留重要文化信息”》,《經濟觀察報》)。這一稱《山海經》為“神話”的看法,無疑受啟於來自西方的“廣義神話”說,值得就其原型意義加以進一步的思考與探討。
這裡補充一句,與“廣義神話”說相應的,是“狹義神話”說,便是把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原始文化形態,統稱為“原始‘信文化’”,原始神話僅為其中之一。“原始‘信文化’”這一新倡的文化人類學的學術概念,將“三位一體,各盡其能”的原始神話、圖騰與巫術三者包羅無遺,三者的共同文化特質,是人類原始宗教文化誕生之前的原始信仰(王振復《原始“信文化”說與人類學轉向》)。葉舒憲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人類學有關神話大概念即“廣義神話”說的理念與方法,他的神話原型研究的視角,顯然與“狹義神話”所倡不一。
神話與歷史:
共同揭示“歷史真實”
所謂“神話歷史”說,由美國學者唐納德·R.凱利首先提出,初見於其《多面的歷史:從希羅多德到赫爾德的歷史探詢》(1999)一書。該書指出:“神話代表著‘希臘人的全部精神原料’,因此是歷史本質之所在。”這就無異於說,神話與歷史,在本質上是同一的。21世紀初,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約瑟夫·馬裡撰寫了《神話歷史》一書,認為唐納德·R.凱利在其著作《蘭克時代的神話歷史》中“將神話歷史作為反對蘭克學派之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統治地位的修正主義運動而提出來”(見葉舒憲、譚佳《比較神話學在中國》)。“神話歷史”這一新的學術概念,是人類學而非傳統文學意義上的。這也便是說,人類學所認同的“神話”,是就整個人類文化而言的,而且兼屬於歷史學的一個范疇,它蘊含著人類的“全部精神養料”,因而是“歷史本質之所在”。
葉舒憲的神話原型批評,接納了來自西方的“神話歷史”理念,主要用於研究關於原型的中國神話與歷史相系這一學術課題。他指出:在原先強烈的“學科本位主義束縛下,神話概念只是在文學學科內得到合法地位和相應的研究”,這就遮蔽了從人類學探究中國文化原型的可能。從人類學神話原型說這一角度看,神話的文化性與歷史的文化性相契,因此,“‘歷史’和‘神話’相互分割對立的僵化局面”必須被打破。的確,“神話的內容和神話講述活動本身都顯露出充分的歷史性,歷史敘事中也顯露出充分的神話性”(同上)。
這一學術判斷,我們應當如何認識與評說呢?譬如,漢代大史筆司馬遷撰寫的皇皇巨著《史記》,是從撰寫神話傳說中的五帝及其時代開篇的,關於黃帝、顓頊、帝嚳與堯舜等的“生平事跡”,都作為“歷史”來寫。太史公曾批評那種“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的缺失,稱其自己曾經“西至空桐(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經過了廣泛的“田野考察”,等於認為其所寫的《五帝本紀》,體現了歷史的真實,並非出於虛構,因而與諸子百家所寫的“黃帝”之類不一。司馬遷自然不懂得什麼是文化人類學意義的神話學,但他將關於五帝的神話傳說,當作歷史真實來寫。他真誠地相信,五帝是真實存在過的,否則,他不可能排出一個黃帝的族譜來。
問題是,《五帝本紀》所記載的,真的是關於黃帝等遠古聖王的一部純粹的“信史”嗎?假如神話等於歷史,就可能泯滅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實際上,遠古的“聖王”事跡,往往有著神話傳說的成分。歷史是關於曾經存在過的人物、發生過的事件等有關具體時空的記述,絕不允許無中生有、憑空虛構。神話則不然,無論是文學抑或人類學意義的神話,恰恰都是以天馬行空式的想象、幻想、夸張與虛構為其生命的。可是,人們也許忘記了,虛構的神話,先以口頭繼而以文字記載的方式存在,本來便是人類遠古生活的事件之一,理所當然是人類歷史的有機構成。歷史與神話作為人類文化現象的兩大極端,都以人類的原始生活為場域,在揭示“歷史真實”這一點上攜起手來,形成“對話”。因而,在筆者看來,當我們以人類學的“神話歷史”觀進行研究時,應當承認:神話與歷史的人類學關系是既合二而一又一分為二的。
有西方學者把“神話歷史”定義為“一種混合著虛構的寓言和傳說的歷史”,葉舒憲認為這是可取的,指出“神話歷史”說“預示著比較神話學將取得以往從未有過的學術跨度與大拓展的知識條件”(《比較神話學在中國》),以為“神話歷史”說最有創意的一個方面是提出文明之前的歷史是由原始神話參與創造的,這一看法,學理上可以成立而且很有見地。某種意義上,原始神話等同於人類的上古歷史,神話與歷史作為敘事,一定條件下存在著“合二而一”的一面。
神話與歷史的關系還有另一面。神話所記述的,遠遠不是人類原始生活的全部,神話一定遺落了生活中的許多東西,歷史所可能覆蓋的面,要遠遠超過神話,神話所揭示真實的敘述方式,也殊異於歷史。這同樣可以証明,神話既等同於歷史又有異於歷史,兩者的關系,確實是合二而一又二律背反的。
就原型探討而言,葉舒憲認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口頭神話、書面神話,都經過了“N級編碼”,盡管那種真實本然是一種“在”,其神話言說卻往往是扑朔迷離的,難以徹底了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在”以及其何以“在”。因此,我們必須如王國維那樣,“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認真、細致、科學地互相參証。
就神話原型來說,值得加以厘清的有:是真正原型意義的原始神話,還是次原型或次次等原型意義的神話﹔是關於神話的最原始的虛構,還是無數次虛構之后的虛構,等等。
葉舒憲所從事的這一學術領域,由於他與許多學者的共同探索,確實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為原型意義的“神話歷史”研究提供了學術創新的可能。然而,這一學術領域所涉及的“人類學難題”頗多,難以做到畢其功於一役。葉舒憲說:“未來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其一,如何採用神話歷史新視野去全面解讀中國的‘二十五史’?其二,神話歷史的觀念如何在‘大歷史’和‘小歷史’之間拓展出更加完善的分析范式與概念工具?其三,神話歷史的觀念如何促進從‘中國歷史’到‘神話中國’的研究范式轉換?”(《比較神話學在中國》)凡此關乎神話歷史的真實與原型問題的發問,確有開拓學術思路的一面。
中國玉:
玉成中國
葉舒憲的學術研究,大致經歷了兩大階段:其一,從文學轉向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這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僅僅是一個短暫的“序幕”,卻並非可有可無。他所說的“文學人類學”,實際是文化人類學,他的神話學觀念,歸根結底屬於人類學﹔其二,以西方人類學關於神話原型說的譯介為契機,先是利用文獻進行了諸如《山海經》等的神話原型批評,揭示譬如《山海經》的有關記述與甲骨文“四方風名”的對應等,繼而轉向“中國玉”這一東方獨異之“靈物”的神話原型批評,注重與西方神話原型說的比較,堅信可以從遠古神話意義的這一神異之“靈物”,追尋中國文化的根因根性,即其歷史與人文原型。葉舒憲所主要從事的,是關於文化“物態”而非文化“形態”的人類學研究。
葉舒憲抓住了“中國玉”這一特殊文化的“中國問題”,他的學術期待首先在他與著名學者蕭兵等亦師亦友、合作良久而取得的不少成果中體現出來,一定程度上,這些成果變革了從謝六逸、聞一多、魯迅、茅盾到袁珂等學者的研究理念與方法。研讀英國文化人類學家弗雷澤的《金枝》和《〈舊約〉中的民俗》等西方人類學經典,是葉舒憲由文學研究轉向人類學關於神話原型批評的一大學術契機。他說,“從那以后,我就迷上了人類學”。
這一個“迷”字,生動地凸顯了葉舒憲一貫的學術態度。無論做任何學術,一位學者的精神境界假如能夠進入虔誠的迷戀狀態並且鍥而不舍,倘若做到孔夫子門生子夏所言那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的境地,那麼他離學術上的大獲其成,可能也就不遠了。葉舒憲是一個願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他的學術經歷也再次雄辯地証明,王國維所說的“學無中西”(《國學叢刊序》)一語,作為研究理念與方法,是具有一定真理性的。在中國學界,以“西”釋“中”還是以“中”釋“中”,一直是有爭論的。誠然,這一“學無中西”、以“西”釋“中”之“學”,應是批判地看待西學而努力結合本土進行研究,而后才可能有所創獲。
葉舒憲關於“中國玉”的文化原型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持續近五年、完成了15次探玉考察。這一“准田野”(有別於考古人類學的田野發掘)的考察活動,覆蓋我國中西部七省區的260個縣域,對史前玉器和玉料產地進行數據和標本採集,推出了三套叢書和電視紀錄片,提出了“4.0版”西玉東輸歷史。
從西方人類學研究史看,田野調查這一人類學的理念與方法,大約始於1846年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北美易洛魁部落的“田野作業”。此后,英國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將其提升為西方功能主義人類學的方法論而受人尊重。人類學研究重視“田野調查”,但人類學研究又不僅僅是“田野”。無論“田野”還是“書案”,關鍵在於真正踐行“科學”二字。我國的歷史學領域,曾經有“疑古”與“信古”兩大潮流,應當說,二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科學因素在,未可一概否定。然而在根本意義上,值得大力提倡的,歸根結底是科學的“釋古”。當今諸多學者,包括葉舒憲教授,都為此而努力實踐著。
做學問,殊為難得的是達到歷史與邏輯、實証與理念的真正統一。假如沒有邏輯,世界便雜亂無序,根本不會有學術理論與思想的系統建構。一旦不注重實証,則所謂的理念與理論“建構”,便會因缺乏學術上的真正洞見而淪為無根的“研究”。對於神話原型批評而言,也總是歷史、實証優先的,這是一個鐵律。在某些學術偏於空疏而無當的今天,葉舒憲等重視並踐行田野考察,謹嚴治學,這種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葉舒憲教授有高遠的學術抱負,對一些現存的學術之見,往往投以質疑的目光。是的,學者首要的學術能力,首先在於自覺地意識到,學術上凡是已經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歸根結底,是“問題意識”催動其進入研究歷程,而后才有解析、實証和解決問題的可能。這証明,所謂學問,“問”比“學”更為“本體”,對於學界不時提出的新命題,唯有在不斷進行實証與理念相統一的研究之后,才可能判斷其真偽、是非。葉舒憲提出、論証過諸多學術命題,如“大傳統、小傳統”與“四重証據”說等,這些是屬於治學方法論方面的﹔又如,他認為在青銅器時代之前,中國有一個“玄玉時代”,提出“玉成中國”與“原型編碼”說等等,凡此都是葉舒憲學術思維頗為活躍的明証。
這裡僅就“大傳統、小傳統”說略言幾句。他說:“什麼是大、小傳統呢?我們針對雷德菲爾德的概念,反其意而用之:將漢字編碼的書寫文化傳統,即將甲骨文、金文以及后來的這一套文字敘事,稱為‘小傳統’﹔而將先於和外於文字記錄的傳統,即將前文字時代的文化傳統和書寫傳統並行的口傳文化傳統,稱為‘大傳統’,比如崇拜玉、巨石、金屬(青銅、黃金等——原注)的文化等。”(《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這種“反其意而用之”的學術思維,是“接著講”兼“反著講”。他將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鄉民社會與文化》一書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場,把文字書寫傳統視為大傳統,把無文字的鄉民社會看作小傳統”的看法,加以改造而自裁新見,顯示出他的學術眼光。
葉舒憲將人類無文字的文化傳統稱為“大傳統”,強調了這一傳統的“原生”意義。這裡的“大”,甲骨文意義為“本始”“原始”,它與人類有文字之后“小傳統”的“次生”性,有本次之別。筆者以為,后起的“小傳統”文化,對“大傳統”必然總是有所遺忘、有所選擇、有所“遮蔽”,然而“小傳統”作為“子”文化,除了“遮蔽”,同時還有“開顯”的一面,不可能與作為“母”文化的“大傳統”毫無關系。某種意義上,“小傳統”是“大傳統”具有真理性意義的文字記憶和表述,必然賡續文化“大傳統”的諸多文化血脈。關於這一點,葉舒憲教授表述為“小傳統之於大傳統,除了有繼承和拓展的關系,同時也兼有取代、遮蔽與被取代、被遮蔽的關系”(《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他的著重點在於強調“小傳統”對“大傳統”的“取代”和“遮蔽”,目的在於凸顯神話原型批評、原型研究的不可替代性,是可以理解的。而“小傳統”中,同樣蘊含著文化原型的因素,同樣不可忽視,關鍵在於要有一個科學的立場和操作。
一個有學術理想、追求實証與理念相統一的學者,在尊重實証的前提下,首先得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然后才談得上始終以實証兼邏輯的方式,加以証是或証非,這便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証”。葉舒憲教授提出的一些學術命題,是在有所實証的前提下提出的,而這裡值得進一步思考、討論與加以實証的課題甚多。實証與理念相統一的追攝,是一個無盡的認知、實踐過程,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實証、理念以及兩者達成真正的統一,是把握學術真理的必由之路。
葉舒憲專注於靈玉這一史前之“物”的神話原型批評,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並未阻塞其他與此不一的研究視角、方法和途徑。筆者相信,為了實現如原交通大學老校長唐文治所言“做第一等學問”的崇高目標,多種學術見解之間的探討甚而爭辯,是必要且理所當然的。
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