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魏六朝總集編撰與文學批評”項目負責人、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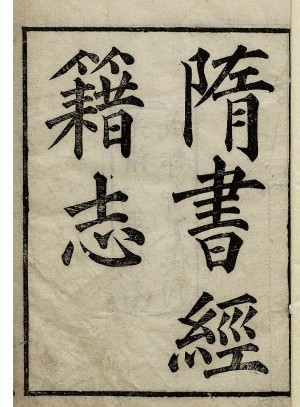
《隋書·經籍志》,國家圖書館藏成都御風樓清光緒八年刻本。作者/供圖

《隋書·經籍志》,國家圖書館藏南京國子監明萬歷二十三年刻本。作者/供圖
《隋志》總集之部是對中國古代總集編撰成就的一次集中總結和展示,著錄了漢魏至南北朝時期的總集,其存者107部,通計亡書合249部,數量極為可觀。這些總集,有集多人之作成集者,更有不少個人著作和單篇作品,情形極為復雜。考察這些總集的歷史狀況和存在情形,可以明確早期人們的總集觀念以及在此觀念下的總集編撰實踐,由此窺見其形態特征,為時下方興未艾的總集編撰提供有益的借鑒。
漢魏六朝的總集觀念
現今關於總集的觀念,一般是贊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將總集分為兩類,一是總眾家之作而集之,二是選眾家之作而集之。但是,仔細考察漢魏六朝人們對總集概念的描述,我們發現,它與現行的觀念並不一致。關於總集,《隋志》的討論隻集中在“採擿孔翠,芟翦繁蕪”一項,顯示其總集概念的中心內涵乃是“選”而非“總”,集多人之作並不是那時總集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鐘嶸《詩品序》也反對總而集之,認為總集如果只是“逢詩輒取”“逢文即書”,沒有“選”的過程,缺乏批評的功能和意義,是沒有多少價值的。蕭統《文選序》指出,編撰總集的目的是通過“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艱苦勞動,呈獻給讀者最精華的文學作品,使讀者減少盲目性,避免不必要地浪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閱讀精華的文學作品中獲得豐富的文學營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徐陵《玉台新詠序》認為,“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諸麟閣,散在鴻都”,如果不做“選”的工作,作為閱讀對象的后宮婦女因囿於性別和身份,很難有機會像男性一樣去一一接觸這些文學作品。正因當時社會對總集“選”的特征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所以蕭繹從繁榮、發展當代文學創作的角度出發,對具有“選”這一特征的總集的編撰給予了更多期待。他認為,文學創作迅速發展,“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固然可喜,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是這些作品美弊並存,媸妍相雜﹔二是卷帙浩繁,讓人“翹足志學,白首不遍”。因此就希望有“博達之士”能夠做“品藻異同,刪整蕪穢”的工作,以一個很好的標准和尺度來衡量這些作品的優劣,去掉繁雜,選取精華,為讀者提供一個精良的讀本。
這些情況表明,漢魏六朝時期人們編撰總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即擔負起文學教育的責任和義務,為培養文學創作人才、繁榮文學創作服務。基於此,人們為總集編撰所定立的原則和標准就自然是“選”而不是“總”,要求其中充滿強烈的經典意識和文學批評色彩,能給讀者以很好的指導,提高其文學素養和創作水平。《隋志》總集“選”的觀念實際上就是對魏晉南北朝形成的這種比較成熟的總集觀念的繼承和發揚,時人就是從這一觀念出發來確定總集、為之編類的。
個人著作的總集特征
《隋志》總集所著錄的個人文學作品集,計有十數種之多,諸如《毛伯成詩》、江淹《擬古》、應璩《百一詩》等。按現代總集觀念,總集至少應該是集兩人以上的作家作品,而這些集子僅是集一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不得序入總集之列的。但是,早期總集概念的中心內涵乃是“選”而非“總”,這就意味著現代總集概念中最重要的元素——集多人之作並不是那時總集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集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專選某一個作家的某一類作品。在選家眼裡,這些作家的這一部分作品在當時具有相當突出的代表性,內容或體制上都極為特出,有一定的示范意義。唯其如此,才把這一部分作品編輯成集,以為述作之楷模,向學界引薦、推廣。如江淹《擬古》,選家將其裒為一集,就是集中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意見,表其為擬古詩的正宗,立為擬古詩創作的典范。又如崔光將其《百國詩》自編成集,顯是以自己能作這樣的詩而感得意,必欲將其自我經典化,示之於人而后快。其事之著見於史,也足見這個集子當時就已引起了轟動,獲得了讀者一定程度的認同。而各家的奏事、啟事、露布文之類之所以被選家編選成集,也無不緣於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在內容或體制上確為特出,具備了文學典范的價值。
從這方面來講,這些個人作品集的形成是充分體現了總集“選”的原則和要求的。至此,我們對當時總集的概念也就有了更為深入而透徹的了解,由於視“選”為總集的靈魂,在並不強求集多人之作為總集之必要條件的前提下,選,就可以是選多人之作成集,也可以是選某一個人的某一類作品成集。但條件是,所選的這一類作品必須富於經典性,是當時推出的具有一定示范意義的作品。
除此之外,《隋志》總集還著錄了不少個人詩文評著作,此如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摯虞《文章流別志論》等。這些著作除了是個人的制作外,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並沒有收錄作家作品。《隋志》將這些詩文評著作歸入總集是出於何種考慮呢?鐘嶸和劉勰的一些論述應引起我們的注意。鐘嶸曾把《詩品》與謝靈運《詩集》、張騭《文士》並舉,抱怨其“曾無品第”,說明他是把《詩品》等同於具有批評功能的詩文總集,劉勰也說他的《文心雕龍》是在“選文以定篇”的基礎上討論體裁之別,二者關系密不可分。這就明確了詩文評雖是自立文字、不錄作品,但仍然還是要經歷選文以定篇的過程,因而與詩文總集選而集之的方式有了共同之處。區別隻在於,詩文評“選文以定篇”是舉篇最句,詩文選集則須過錄全文。了解這一情形,我們對時人將詩文評著作和文學作品集作為總集著錄在一起的做法也就十分理解了。
毫無疑問,這是承襲了魏晉南北朝人們的總集觀念的一種做法。在時人看來,詩文評著作雖是自立文字,沒有直接收錄文學作品,但它們都離不開“選文以定篇”,這和通過選文來進行批評是同樣的性質。二者的批評形態、方式既同,將其作為總集著錄就是一種不唯合情也極合理的做法了。
單篇作品的總集特征
按照今天的觀念,個人著作固不能稱之為總集,而單篇作品則是一個作家的一篇作品,稱之為總集尤為不可,但是《隋志》總集卻將一些單篇作品目之為總集,這又是為什麼呢?
《隋志》總集著錄的單篇賦注作品,其署名時往往強調的不是作品的作者,而是作品的注解者,說明這些單篇賦注能歸入總集,編者並不是從這篇賦本身來考慮的,而是從賦的注解或音注來考慮的,其文本的總集性質,正在於其注解或音注,因此編目者在著錄的時候,也就忽略掉作品的作者之名而隻署其注者之名了。由此可見,《隋志》之所以將它們作為總集著錄,就在於其性質此時已不是作品而是純粹的批評著作,注者在選文定篇的基礎上發表了對作家作品的批評意見,使文本本身具備了批評的特征和功能。
那麼,單篇賦注又是在哪些方面具體地體現了總集的特征呢?魏晉南北朝注家注賦往往是為了備明物隸事之需,非常注重賦中方物、事類的注解。比如徐爰注《射雉賦》,主要是因為此賦所寫之物世“昧而莫曉”,而自己恰好又很熟悉,於是就以己之所聞注解了這篇賦,希望能夠備世之遺忘。可見單篇賦注已被視為總集的一種形式,注家是有意要把它做成一個文與事類相兼的文本。其總集特征的具體表現,正在於其文兼事類的獨特注疏方式,它以這種方式表達了對作品的批評和見解,也以這種方式惠予了學者事類方面的知識。
單篇賦注作品而外,《隋志》總集還著錄了一些單篇無注的白文賦作,諸如傅毅《神雀賦》、梁武帝《圍棋賦》、張淵《觀象賦》、張居祖《枕賦》等。這類單篇無注賦作都是以某一種物類為題材進行創作,說明在時人的觀念中,可以視作總集的,實際上隻限於事類賦,其他的則不在其列。因其內容是明物隸事,具備了類書或志書的特點,體現出了應用的價值,於是時人就把它們作為類書或志書揀選收藏,以備作文事類之需。即此而言,這些專賦事類的單篇賦作就大可視為總集的“事出於文”者流,先天即具備了總集的這一特質。時人將這些單篇無注賦作視為總集,顯然是從它的這種總集特質來考慮的。
當然,也不是所有明物隸事的單篇賦作都可以視作總集,它們能否成其為總集,也還是要經歷一個選的過程,就是社會的選擇和接受,而流傳則是檢驗其為社會所選擇、接受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如傅毅《神雀賦》,當時漢明帝曾詔百官賦神雀,然“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可見傅毅的作品之所以被時人所選擇、接受,正在於它是同題作品中的“金玉”,而其他作品之所以被淘汰,則在於其“文皆比瓦石”。又如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作為文學史上的經典,它被社會的選擇和接受在背后更有諸多動人的故事。據《后漢書》,蔡邕欲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在三國時代,生活奢靡的蜀國貴族劉琰因好《魯靈光殿賦》,曾悉教數十侍婢誦讀之。晉代阮孚,以其母為胡婢,其姑因取《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句中的“遙集”二字作為他的字。在南朝,顏之推教導諸子,稱自己“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這就表明,這些單篇賦作得以流布,絕非偶然,世人的普遍認同,才是它們得以存在、流布的根本原因,它們貌似白文無注,其實每一篇都大大地寫了一個“選”字。
綜上言之,漢魏六朝總集編撰其實並不是貴族文人文化奢侈品的制作,而是一種文學發展動能的制造,目的是驅動中國文學這艘巨輪,使之劈波斬浪,不斷前進。今天,在盛世修典的熱潮中,各種文學總集編撰方興未艾,但大多鐘情於網羅放佚而鮮少留意於採擿孔翠,從保存文學文獻的角度來講,其行固可嘉尚,但又何妨選盛登臨,考慮擔當一些文學教育的責任,致力於文學經典的建構,為當下的文學發展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