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衛娟,系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講師、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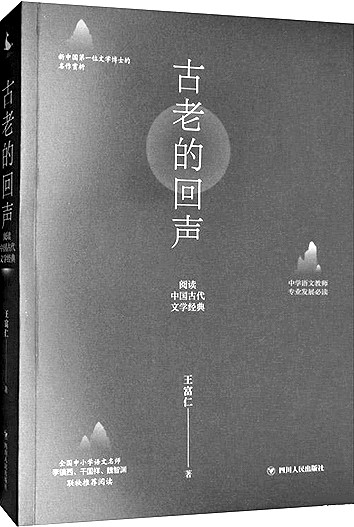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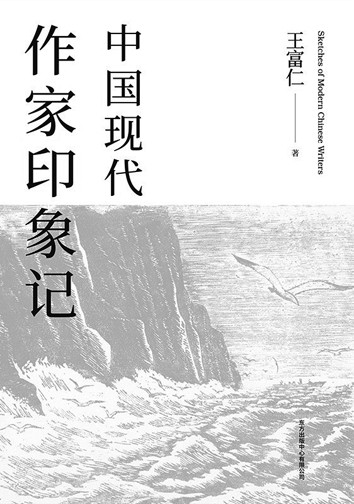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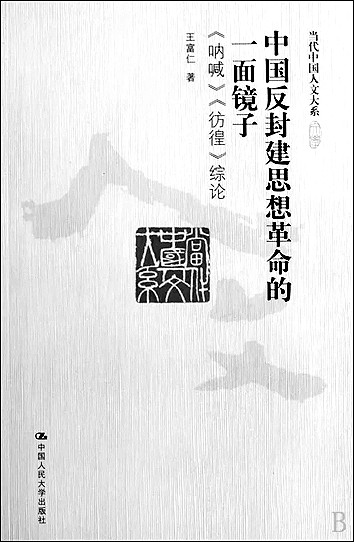


王富仁(前排左)與西北大學同學合影 資料圖片
【求索】
學人小傳
王富仁(1941—2017),山東高唐人。1967年本科畢業於山東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1981年碩士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1984年博士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語文教學與文學》《古老的回聲》等。
20世紀90年代末,語文教育界有一次涉及語文教材、教師、教學、評價等各個層面的大討論。這次討論成為一個契機,使得語文——這一關乎民族文化傳承和人文素養培育的學科——再次進入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在這些研究者之中,王富仁是介入程度最深、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
與一些學者較為注重學生基本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的思路不同,王富仁自始至終都在思考文學在語文教育中的意義和價值。他嘗試用自己從事文學、文化研究的治學路徑,澄清困擾語文教育的基本問題,嘗試用自己敏銳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打通“人與語文”的情感維系,探究語文學科獨特育人功能的發揮與實現。
對於王富仁而言,對語文教育的持續介入,是他的人生經歷、責任意識和研究思路綜合作用的必然。
直面作品——
在語文中培養情感
王富仁1941年出生於山東高唐,自幼喜歡讀書,初中時就讀完了《魯迅全集》,自此愛上了文學、愛上了魯迅。魯迅,也成了他的精神導師,在此后動蕩、波折的歲月中,王富仁始終保持著清醒與獨立,保持著勇於探究真相的熱忱與激情。
王富仁是新中國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第一位博士,在文化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語文教育研究多個領域碩果累累。然而,在十分注重“著史”的現代文學研究界,他卻從未參與過文學史相關的寫作。相比“史”的建構,他更想做的工作,是“去蔽”,通過文化研究、魯迅和其他文化學者的比較、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甚至文本細讀,發現並走進真實的文化、文學史、文學作品,從而關注現實的人生,走進心靈的真實。
王富仁做了大量“文選”類的工作。他主持編撰了新詩選、現當代短篇小說選、歷史小說大系等書籍,並充分肯定了“選本”的意義與價值,試圖整理真正能夠成為經典的當代文學作品,服務於普通大眾讀者——這對現代文學的接受、傳播和經典化意義重大。他的選本或作家作品導讀,也致力於“去蔽”,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和感受,引導讀者的心靈和作家作品實現近距離的溝通與交流。比如他對不同詩人詩歌的品讀,十分注重感受詩人們的“個性”“獨立風格”,即回到詩人本身,回到“真的人”來談論作品。例如,他認為,同是新月派的聞一多和徐志摩,詩歌語言給人的感覺其實截然不同,“聞一多的詩的語言像一塊塊鐵錠、鋼錠,硬硬的,冷冷的,把方塊漢字的重量感幾乎發揮到了極致”,而有重量感的中國漢字,到了徐志摩的詩裡,則像鵝毛一樣輕。從這樣的感覺出發,前者凸顯的是聞一多其詩其人的沉重,后者則表現了徐志摩的瀟洒。順著此思路,王富仁在2002年為中學生導讀了曹禺的戲劇《雷雨》,既在相對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中外戲劇的比較中闡釋曹禺戲劇創作的重要意義,更將《雷雨》視為曹禺感受人生、感受社會的產物,認為這部劇作把對人、對人類的同情推向了新的高度。
雖然王富仁的主要興趣是現代文學研究,但他在20世紀90年代寫作了一系列古代詩歌賞析類的文章。這些文章基於自身切實的體驗和感受去品悟古詩,可讀性很強,后來結集為《古老的回聲——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被列為中小學教師的基礎閱讀書目。這部書中的文字,仍然強調回到本真,和文本進行直接的心靈溝通,而不是被古往今來那些先驗性的結論或研究成果所左右。比如《江南》(江南可採蓮)一詩,王富仁從中讀出了魚戲蓮葉的活潑和靈動,以及其中洋溢著的自由美好的情思。有人援引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勞動愉悅說和愛情隱喻說,與王富仁爭辯,王富仁提出了下面兩個問題,集中體現了他閱讀文學作品時對直覺、真實感受的重視:“一、你的這種想象是在初讀《江南》一詩的時候便產生的呢,還是在讀了別人的研究文章之后才根據研究文章所提示的觀念向該詩作出的比附性想象呢?二、假若你現在拋開別人研究文章的一些提示性說法,直接將你的結論與閱讀原詩的感受相對照,你覺得你的解釋與原作的韻味‘隔’呢,還是‘不隔’呢?”(《古老的回聲——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
王富仁這種注重本真體驗的古代經典重讀方式,從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詩意境界入手,將自己的心靈直接沉浸到詩歌所傳達的豐富心理變化和繁復意蘊當中,讓豐富的內心感受與詩歌本體所傳達出來的生命體悟直接對話,因此讓語文教師讀來“不隔”,給他們諸多啟發。
王富仁的文學研究,從小說起步,兼顧戲劇、新詩、古詩詞,從魯迅開始,但並不停留在魯迅,而是延宕到其他文化名人、文化思潮。他從不被已有的框架所禁錮,就是因為他從不把某種文學理論放在首位,從不把某些研究成果視為理所當然,他的研讀、思考、寫作的起點都是自我的獨立判斷。
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路,他注意到了語文教育在直覺、情感培養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當其他課程主要培養學生掌握和運用知識性、科學性、邏輯性的語言素質的時候,中小學語文教學則理應主要培養學生掌握和運用直觀的、直感的、感情的、審美的語言素質的能力”(《情感培養:語文教育的核心——兼談“大語文”與“小語文”的區別》)。同樣,隻有那種運用了“直觀的、直感的、感情的、審美的”語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才有真正感人的力量,才具備與人心靈溝通的“可感性”,應該成為語文教育的主要載體。
王富仁的這一觀點,直接啟發了2001年語文課程改革之后注重“體驗、感悟”的教學方式——有時候,我們讓學生在文學作品中真正體驗到、感受到某種情感,豐富了他們的情感、經驗和體驗,就已經達到了教學目標。這其實就是文學教育“潛移默化、熏陶感染”的作用,這也是王富仁一直在探求的“人”的教育的實現路徑。
跳出語文——
培養獨立完整的人
閱讀王富仁關於文化、作家作品研究和語文教育的諸多文章,我們會發現,他常常在相對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梳理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王富仁1967年從山東大學外文系俄語專業畢業后,曾在中學執教多年。學俄語出身,這時候卻陰差陽錯地被分配去教了語文,王富仁竟然如魚得水,做得有聲有色。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候的語文教育,沒有系統的考核和嚴格的教學安排,無形中給了語文教師較大的自主權。而語文教科書中的文學作品,很多是王富仁一直痴迷的魯迅作品。在這種情況下,王富仁毫不猶豫地把教學主要放在了講讀魯迅上,據他自己回憶,一篇《祝福》甚至能講上三個星期。王富仁青少年時的閱讀積累,以及過人的文學作品感受力、理解力,開始顯露出來。此時,王富仁遇到了人生中的伯樂——魯迅研究專家薛綏之先生,開始撰寫解讀魯迅作品的文章,並參與編撰薛綏之主持的《魯迅雜文中的人物》。二三十年后,王富仁以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全面介入了語文教育——參加語文教科書的編撰、撰寫語文教育相關研究論文、指導語文教育學研究生,提出“教師主體性”,理論高屋建瓴、發言專業內行,與這段從教經歷不無關系。
1978年,王富仁考上了西北大學單演義的碩士研究生,此后又在北京師范大學李何林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他對文學的感受和研究,逐漸從散點化的、細碎的品悟,上升到了系統化、理論化的層面。王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當時在學術界反響很大,至今仍然堪稱經典,這些論文初步形成了王富仁的研究思路——把研究對象放在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考量,已經顯示出一位優秀學者在宏大命題中縱橫捭闔的氣勢,而充盈其中的熱情、執著與真誠,讓人們仍能領略到那位教學率性、理解文本“任性”的語文老師的風採。
1984年,王富仁留北師大任教,先后發表了多篇文化研究的論文。據他自己后來回憶,他是希望通過文化的透視,來“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時代,認識自己時代的文學”。值得一提的是,王富仁從不生搬硬套某種理論,而是把理論消化吸收為自我的一部分,形成了獨具王富仁特色的分析方法。比如,在《文化危機與生產過剩》一文中,王富仁聯系整個社會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提出文化發展的周期性問題——文化也有復蘇、發展、繁榮、蕭條等不同發展階段,而在不同階段裡起主要作用的是不同的知識分子。這篇文章在整個文化史中思考當代知識分子的意義,以此來反思文化,重估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自我價值實現的方式。自然,這一研究方法也被移植到了王富仁的語文教育思索中——在異常宏大的學術視野背景下展開論述,論述當中隨處可見反思與批判精神,有直面靈魂的真實,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誠如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所說,王富仁的探索、思考和質疑,總是在不斷追問,“這是真的嗎?這是從生活裡、從生存的意志裡來的嗎?這是真正發自內心深處、能夠體現整個民族生活的總體需求的訴求嗎?”(汪暉《竦聽荒雞偏闃寂》)
時代在變化,語文教育改革幾乎每十年進行一次,學過蘇聯,也參考過歐美,可是,到底為什麼要改革?王富仁在關注語文教育之初,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寫了《當前中國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的歷史根據》,將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置於整個中國教育發展演進的歷史變革中,分析了傳統語文教育模式在不同時期的作用和局限,進而指出,當前語文教育與社會發展要求產生了矛盾,注重工具理性的方法破壞了中小學語文教育應有的感性審美生態。在20世紀末的語文教育大討論中,人們批評語文教育盲目追求應試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扼殺了學生的性靈。然而,這只是教育改革的表面原因,王富仁從現象尋根問底,從教育史和人才培養模式的角度,將語文教育的問題視為一種文化現象,來思考語文課程改革的依據:社會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要求語文教育培養“人”、解放人的心靈才智了。
也就是在此背景下,諸多學者重提魯迅的“立人”說——“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文化偏至論》),在發揚人的心智個性基礎上,鼓勵個體的人具有完善自己與發展社會的永恆追求。這無疑也是王富仁一直在思考、探尋的教育理想。那麼,語文究竟應該怎樣,才能培養真誠、獨立、完整的人呢?王富仁又在宏闊的歷史文化的脈絡中,分析了“語文”的內涵。相比於古代的“大語文”教育,今天的語文,應該是“小語文”教育,區別於其他學科的根本,在於其情感、審美價值。這樣的定位,使得語文的教育功能大大聚焦,人們開始思考,立足語文學科本位,給語文“減負”的同時,真正發揮其獨特的育人功能。
語文教育究竟何去何從?這不是一個學者能夠決定的,但王富仁尋根問底的研究思路,震動了語文教育界,促使該學科更加深入地探求自身理論建構的路徑。
不做“教書匠”——
提倡教師主體性
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王富仁在全面介入語文教育之后,將現代文學傳統中的文學教育觀念和理想,付諸語文教育中。
2002年,王富仁到汕頭大學任教,提出並建構了“新國學”的理論體系。“新國學”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中、在“國學熱”的現實環境中產生,最關注的是現代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文化體系中的位置。王富仁試圖將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建構成一體化的關系,也就是“由民族語言構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整體”,共同鞏固中華文化的地位,使之成為能與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因子,“永遠堅持民族語言的母語地位”,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同存共棲的歸宿地”(《新國學論綱》)。而在這個母語學術整體中,王富仁最為推崇的,是屈原、司馬遷、曹雪芹、魯迅。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四個不同但又真正具有獨特精神價值的偉大人物。
作為魯迅研究者,王富仁和魯迅一樣,“時時刻刻不忘解剖我自己”,經常反思和批判自己。他對人民大眾有一種責任意識,就像魯迅所期望的那樣——要做“民魂”,不斷推進民族的前進,“肩起發展中華民族的各項文化事業、謀求中國社會的進步、推動中國歷史的持續發展的歷史責任,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在他看來,從事基礎教育教學的語文教師,承擔著用教育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和使命,應該考慮學生的終身成長和長遠發展。可是,不少語文教師的教學跟著課標、教材亦步亦趨,不越雷池半步。語文教師,不應該成為“教書匠”啊。學生呢,成了紙筆考試的工具,人雲亦雲鸚鵡學舌,缺少靈性和才智,缺少自己的獨立性和判斷能力。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魯迅鼓勵青年“說自己的話,而不是他人的話”。
王富仁清醒地看到了當時教育存在的一些問題,在1997年就提出要解放學生的思想,讓學生自由表達,在大膽真實的表達中培養健康的人格,他甚至期待一種純粹的“兒童就是兒童”的自由世界,將兒童視為一個獨立成長的個體,自在發展兒童的靈性與感性,真正將魯迅的“幼者本位”落到實處。但他很快發現,沒有教師的主體性,學生的主體性更無從談起。因此,王富仁寫作了一系列與教師主體性相關的文章,大力提倡“教師主體性”的實現——“教育就是讓一個已經有了獨立生存和發展能力的成年人輔助學生成長,使他們成長為一個有獨立生存和發展能力的成年人,然后進入到社會工作、社會矛盾、斗爭中去爭取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決定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體性。”(《我的語文教學觀》)
這裡所說的教師主體性,其實就是主張教師應該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情懷,在對學生的真正關愛中,“為之計深遠”,而不是局限於由考試成績決定的收入。
王富仁認為,語文教師的教學主體性,體現在對文學作品的透徹把握和理解方面,在此基礎上,語文教師才能和學生一起體驗、感受,與偉大作品對話,用經典文學作品的可感性,打造能夠豐富學生情感、蕩滌學生靈魂、提升學生精神境界的文學課堂,在潤物無聲中培養德才兼具的大寫的人。
在王富仁的整個人生經驗和學術體系中,魯迅研究是他的核心,也是他的學術生命所系,對語文教育的關注,看似是他學術活動中的插曲,實則是學者性情、責任意識使然,是產生實際影響最大的領域。語文教育學者潘新和認為,王富仁在語文教育領域的問題意識、理論建構發人深省,“作為魯迅專家而不囿於魯迅,特立獨行、無所依傍。他不但是現代文學界的旗幟,也應該成為語文界的旗幟。”(《語文:審視與前瞻——走近名家》)
可以說,在文學研究和語文教育之間,王富仁的思考和探索,今天讀來仍然振聾發聵。這是因為,王富仁一直堅持做下來的,用“去蔽”來尋求真相、堅持尋根究底的學問意識,持之以恆的對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追求,具有深遠的意義。王富仁給文學研究和語文教育帶來的,應該是一個倔強、執著、真誠、坦率、熱情的靈魂吧。
據說,王富仁生病住院那段最后的日子裡,經常讀的一本書是《杜威論教育》。教育啟蒙的理想,是否就是這位文學研究界的思想啟蒙者,心靈最后的棲息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