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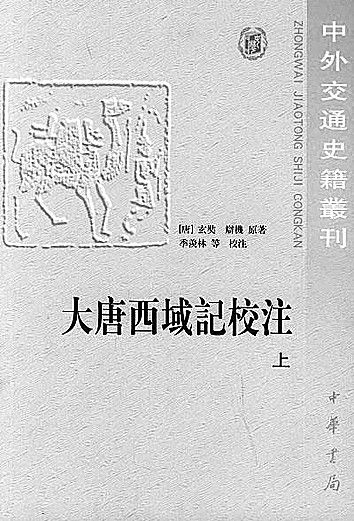
季羨林著作

季羨林著作

季羨林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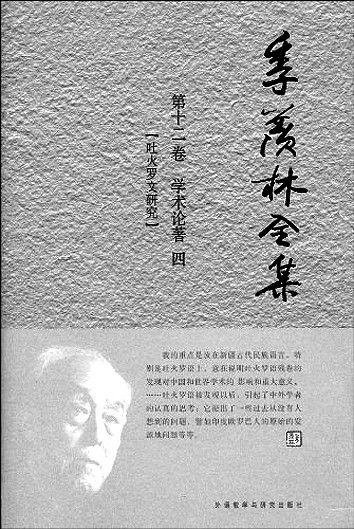
季羨林著作

2001年,本文作者(右)與季羨林在一起。 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學人小傳
季羨林(1911—2009),字希逋,山東臨清人。東方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后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1946年回國后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研究領域涉及梵學、佛學、吐火羅文和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等方面。曾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副校長等,曾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等。著有《中印文化關系論文集》《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糖史》《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大唐西域記校注》(合著)等﹔翻譯有《沙恭達羅》《羅摩衍那》等。其著作匯編成30卷本《季羨林全集》。
20世紀80年代初,為團結國內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推動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季羨林先生積極參與策劃、組織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創建工作。從1983年8月學會在蘭州正式成立起,季先生就擔任會長,直至2009年辭世。這26年,學會在季先生的領導下形成運轉的基本格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也突飛猛進,不僅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還在諸多領域取得領先地位。而對於我個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季先生的幫助改變了我的學術人生。
作為會長的季先生
作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先生一直十分關注敦煌吐魯番學的理論建設。他多次強調,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有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而中國古代的敦煌和新疆地區正是四種文化交流匯聚之地,這實際上是把敦煌和吐魯番學研究置於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廣闊背景之下,極大提升了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針對一些學者認為敦煌學不能成為一門學科的看法,季先生撰寫了《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確了敦煌學應該可以成為一門學科,此文后來經過修改成為《敦煌學大辭典》中“敦煌學”一詞的詞條。現在,敦煌學是一門學科的看法已為多數敦煌學研究者所接受。
季先生的另外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提出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這個口號既是對國際顯學敦煌學的准確概括,同時充分顯示了中國學者應有的寬廣胸懷,得到了國內外敦煌學者的一致贊賞。季先生對敦煌吐魯番學的理論貢獻,至今對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永遠值得我們珍視。此外,季先生在敦煌吐魯番學的具體研究特別是胡語文獻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季先生領導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組織協調國內研究力量、人才培養、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資料建設和資助學術著作出版方面都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學會一向支持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組成研究實體,形成合力,進行學術攻堅。現在,除敦煌研究院以外,北京大學、蘭州大學、浙江大學、西北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吐魯番地區都有關於敦煌吐魯番學的專門研究機構。季先生還對浙江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敦煌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做過很多具體指導。學會組織編纂的《敦煌學大辭典》,動員了國內敦煌學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百余位重要研究者參與,是協調國內研究力量進行學術攻關的一項重要工作。這部大辭典有很高的學術性,同時也總結了百年來國內外敦煌學研究的相關成果,出版后得到了學術界極高的評價。顯然,如果沒有季先生這面旗幟,沒有學會出面協調,任何個人或單位都很難有這樣大的號召力和感召力。在人才培養方面,作為會長的季先生可以說是一直在親力親為。他不但長時間招收和指導研究生,桃李滿天下,在扶持國內外中青年學者方面,也是不遺余力。
在季先生任會長期間,學會組織或參與組織了十多次大中型國際或國內的敦煌吐魯番學學術研討會。為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學會還參與策劃和組織了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從這個委員會的策劃到最后組成,季先生都給予及時和重要的指導。隻要可能,凡是學會組織的學術研討會,季先生都會到場講話並參加學術研討。后來因為年高行動不便,不能親臨,他也會發來賀信或視頻講話。現在,國內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的對內和對外學術交流渠道通暢,交往頻繁,與學會成立之初的狀況已經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了。這與季先生和學會的推動不無關系。
在資料建設方面,學會資助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蘭州大學建立了兩個敦煌學資料中心,資助新疆考古所建立了吐魯番學閱覽室。現在,國家圖書館和蘭州大學的敦煌學資料中心都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資料中心。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著作出版困難時期,學會還資助出版了一批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專著和重要譯著。受到資助的著者和譯者后來都成為著名敦煌吐魯番學專家。
《敦煌吐魯番研究》雜志的創辦,亦是季先生鼎力支持的結果。1995年,榮新江學兄在季羨林、周一良、饒宗頤等先生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謀劃創辦《敦煌吐魯番研究》。該刊於1996年正式出版,季羨林、周一良和饒宗頤三位先生任主編,榮新江主持編輯部工作。季先生和饒先生還親自為創刊號撰寫宏文。2004年以后,由我以編輯部主任的身份主持雜志編輯工作。二十多年來,《敦煌吐魯番研究》已經出版了21卷,發表論文和書評1000多篇,很多在敦煌吐魯番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論文都是在這本雜志上首發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用稿以論文質量為准,不論資歷,在提高雜志論文質量的同時陸續向學術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學者,很多青年學者都以在此刊上發表論文為榮。如季先生的學生王邦維教授所言,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和當時仍然健在的饒宗頤先生三位主編雖然沒有參加具體的編輯工作,“但作為我們學術和精神的導師,對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一直給我們鼓勵和指導”。可以說,如果沒有季先生等三位主編的支持,就不會有《敦煌吐魯番研究》。2018年,饒宗頤先生仙逝,《敦煌吐魯番研究》創刊的三位主編均已歸道山,編委會推舉我繼任該刊主編。我是以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心態接下了這副重擔,在編委和學界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目前該刊收稿、審稿、發稿、出版都很順利,仍是受到學界和社會關注的重要刊物。我們編委會成員都認為,繼續辦好《敦煌吐魯番研究》,不斷推動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就是對季先生等三位創刊主編的最好紀念。
扶持栽培中青年學者的季先生
季先生曾對我說過,他“對青年人是有求必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現在國內知名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都曾得到過季先生的扶持和提攜。季先生扶持中青年學者的方式多種多樣,或為他們的著作寫序,或為他們評定職稱撰寫鑒定意見,或為他們申報項目撰寫推薦書,或直接出面為他們解決工作崗位和家庭困難問題,等等。對我的扶持和栽培,就是季先生幫助中青年學者的一個縮影。
1990年,我准備申報國家教委(今教育部)第二批青年專項科研基金。因為我當時的職稱是講師,按規定須有兩名同行專家推薦才能申報,我首先想到了季先生。頭天打電話和季先生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次日我如約按時到達季先生位於朗潤園的家。進門后看到季先生正在和林梅村先生談話,我看先生有事,就想放下材料告辭,心想等先生有空的時候寫好推薦書我再來取。但季先生示意我坐下,他起身來到一個餐桌前坐下,拿起筆就開始寫推薦書。其間,還有其他人來訪,季先生都讓他們等一會兒。不到十分鐘,推薦書就寫好了。我拿到推薦書,心中感慨萬千,既感慨季先生的大家手筆,無需醞釀就下筆成文,又感慨我這樣一個來自地方高校的無名講師,何德何能,竟然得到季先生如此厚愛,享受到了優先接待、立等可取的待遇。此情此景,至今想起來心中還是暖洋洋的。
因為有季先生和沙知先生兩位學界前輩的推薦,我順利拿到了國家教委第二批青年專項科研基金,資助額度為一萬元。當年圖書和設備價格都比較低,一萬元的實際購買力相當可觀,我的好多學術書籍是用這筆經費購買的。對我來說,獲得這個項目資助,其意義不僅是經費的問題。當時申報項目的渠道很少,設置的立項指標也很少,能獲得省部級以上項目的青年教師鳳毛麟角,我成為首都師范大學第一個獲得國家教委項目的青年教師。所以,這項科研基金使我從普通青年教師中突出出來,成為“人才”。這個“人才”的起點,為我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我於1992年破格申請副教授、1994年破格申請教授以及申請博士學位,都是請季先生做鑒定人或評議人。其中有兩次請季先生寫鑒定,正值暑季,酷熱難當。我知道季先生哮喘的老毛病夏天容易復發,所以與他聯系時心中很是不安,但季先生每次都是非常愉快地答應下來,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很快把鑒定寫好。特別是我在破格申請教授的時候,兩年前才被提升為副教授,自覺學術積累還不夠,心中沒底。好在校內有寧可師和齊世榮先生護持,校外有季先生和周一良先生舉薦,最后順利通過了系、校和市三級評審。
此外,我參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領導工作,乃至后來擔任會長,也和季先生的扶持和提前部署密切相關。2001年,季先生年近90歲高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決定在北京推舉一位年輕些的副會長協助季先生。經秘書處和多位常務理事的推薦,季先生同意由我任副會長,和當時的秘書長柴劍虹先生一起負責學會的日常工作。我們沒有辜負季先生的期望,在此后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在季先生領導下保証了學會的正常運轉。這十年的歷練,不僅使我熟悉了學會的運作和管理,也使會員和理事對我有了比較多的了解。季先生2009年7月去世,2010年4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杭州舉行了換屆選舉。當時雖然有好幾位副會長,但年齡都已超過或接近70歲,所謂年富力強的副會長隻有我一個。再加上過去十年,季先生已經放手讓我和柴劍虹老師一起主持學會的工作。就這樣,我在新一屆理事會上,幾乎毫無懸念地當選為接替季先生的新會長。
還應該指出,季先生對我的提攜和栽培,可以說是不次拔擢。就資歷來說,我大學本科是79級,前面有人才濟濟的77級和78級﹔研究生我是83級,前面有78級至82級五屆研究生。那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我前面可以說是黑壓壓地站滿了身懷絕技的高手。如果沒有季先生的不次拔擢,我恐怕是很難露頭的。每念及此,心中充滿對季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感恩之情。
最近二十年來,我自己也參加了很多評審、推薦、鑒定和評議。這使我可以切換視角來認識季先生當年對我的提攜和扶持,逐漸認識到站在被提拔、扶持的位置和處於扶持、提攜的位置,觀感是有很大差異的。以我而論,當了會長以后,會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自己了不起,甚至內心會產生自己就是比別人強的感覺。但如果站在季先生的角度,他其實是有很多選擇的。在他面前,幾位會長候選人之間的差異其實是模糊的。當然,一旦選定,候選人之間的邊界就清晰了,差異就被表面化或標簽化了。我作為被提拔的幸運兒,如果沒有內心的警惕和自省,就很容易滋生“自己很了不起”的想法,也很容易認為這個位置理所應當屬於我。我在這裡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學術界這不是個案。現在學界很多稱號和頭銜都被標簽化甚至物化了,社會上和很多高校、科研單位都把擁有某個頭銜或稱號當作“人才”的標志,甚至作為享受經濟待遇的依據,而獲得這些稱號和頭銜的人,自我感覺良好的也不在少數。其實,評選任何一個學術稱號或者頭銜,在提拔者或評審者那裡,界限也許是模糊的。而且,受諸多因素影響,擁有某種頭銜、稱號的人未必就比其他人強。這樣看來,我作為受惠人,不僅要感恩季先生對我的扶持和提攜,同時還要感恩季先生在諸多候選人中選擇了我。
現在回過頭來看,季先生對我的提攜和栽培,是一套組合拳,包括項目、學位、職稱、學會領導各個方面,涉及一個青年學者成長的各個方面,為我的順利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我並非季先生的入室弟子,由此更可以看出先生的胸懷。季先生就是這樣扶持、提攜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學者,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事業也因此而不斷取得更大的發展。
充滿朝氣的季先生
在與季先生接觸、交往的過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在進入老年以后,沒有一般老年人那種“來日無多”的心態,時常忘記自己“老之已至”。我們都知道,《三國演義》裡有一位不服老的老將黃忠,其言語、行為令人欽佩。但黃忠不服老的前提是承認自己已老,而季先生呢,給我的感覺是,有時他根本不認為自己已老。
記得那是在1995年9月,年過八旬的季先生到首師大做學術演講,學校的學術報告廳坐滿了慕名而來的師生。那次演講的題目是中西文化的異同,演講中,季先生談到跨世紀問題,他語氣堅定地說:“我肯定能夠跨世紀。”在1995年前后,“跨世紀”和“跨世紀人才”是很流行的詞語。但當時人們所說的“跨世紀人才”,一般指的是45歲以下的中青年,恐怕沒有人會把“跨世紀”與八十多歲的老者聯系在一起。而季先生響亮地提出,自己要和中青年一道從20世紀跨入21世紀。季先生的豪言壯語一出,先是滿座皆驚,繼而是熱烈、持久的掌聲。
季先生良好的心態絕非靠豪言壯語支撐,它首先源於良好的身體狀況。有一次和季先生一起吃飯,季先生告訴我,他身體老化的狀況並不明顯,視力、聽力均無問題,最自豪的是手不顫抖,不像其他很多老先生那樣因手抖而影響寫作。這說明季先生的身體狀況比一般同齡人好得多。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季先生的心態和身體狀況都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呢?我猜想有兩個因素肯定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一是積極的讀書和寫作活動激發了自身的生命力,延緩了機體的衰老。一次和王邦維學兄與季先生同行,邦維兄告訴我,當時已83歲的季先生仍堅持每天到學校圖書館查閱資料。他還說,在北大,80多歲的老先生堅持看書的還有一些,但每天去圖書館的恐怕隻有季先生一人。我想,如果一位80多歲的老先生仍具有強烈的研究、創作願望並能身體力行,這種狀態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體潛在的活力,從而起到延緩衰老的作用。其二是季先生喜歡與年輕人交往。一次和鄧文寬學兄聊天,文寬認為先生身邊有一批年輕的朋友,是他很少有老年人心態的重要原因,我深表贊同。
中青年學者願意與季先生交往,是因為季先生喜歡他們,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不遺余力提攜和扶持他們。中青年學者願意與季先生交往,還因為季先生沒有架子。我們與季先生在一起時,感到氣氛很輕鬆,很親切,交流沒有代溝,沒有距離。季先生不僅沒有架子,在學術上還能虛心地征求、傾聽晚輩的意見。記得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季先生邀我和王邦維、鄧文寬到他家,為《敦煌學大辭典》中他撰寫的一個詞條提意見。季先生的學識和成就,學術界早有公論,但就是這樣一位為人們所敬仰的學界泰斗,竟然為一個詞條而專門征求我們幾個晚輩的意見。我們知道季先生找我們來是出於誠心,所以我們幾個也盡自己所知,發表了各自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部分被季先生採納了。提完意見以后,季先生請我們吃飯。那天季先生興致很高,談鋒甚健,我們老少數人其樂融融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季先生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和崇高的敬業精神亦為我輩所敬仰。記得寧可師曾對我談起,季先生為搜集有關“糖史”的資料,曾花費一年多時間把《四庫全書》翻了一遍。我聽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靜。此前,不止聽一個人說過,我們這一輩人之所以很難取得像前人那樣偉大的成就,主要是由於先天不足。對於上述說法,我也曾產生共鳴。現在看來,如果和季先生相比,我們不僅在語言和古代文化素養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先天不足,在后天的勤奮、嚴謹和敬業精神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捫心自問,如果現在需要我翻閱一遍《四庫全書》,我能否做到呢?我不知道。但當時已經年逾八十的季先生卻做到了。我想,隻有將生命和學術融為一體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季先生的行為是對我們后輩的巨大鼓舞和鞭策。當我們在研究中為未能窮盡史料而找出種種理由開脫時,當我們因懶惰而想省略再次核對引文的步驟時,如果能想一想季先生曾為完成一個研究課題而翻遍《四庫全書》,我們的工作一定會比現在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季先生樂於幫助中青年,又平易近人,虛懷若谷,所以他總是擁有一大批中青年朋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中青年朋友,才使得季先生很少有老年人的暮氣,而是充滿了朝氣。
衰老是一種生理現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大量事例表明,心理因素對延緩或加速人的衰老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如果學者們都能像季先生那樣,年逾八十仍能保持中青年的心理狀態,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生理上的衰老、取得更多學術成果呢?季先生不僅在為人和為學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在戰勝衰老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