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明星,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葉紀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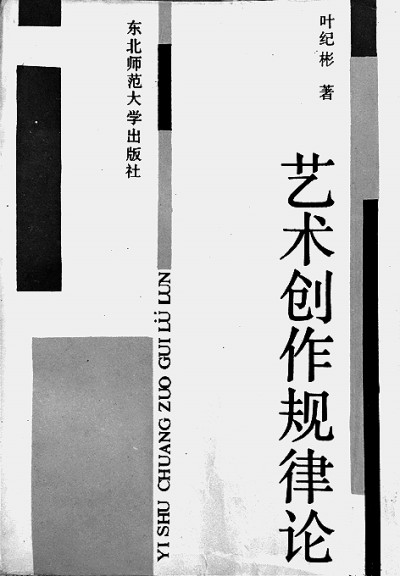
葉紀彬的部分著作

葉紀彬的部分著作

葉紀彬的部分著作
【求索】
學人小傳
葉紀彬(1938—2021),筆名荊溪,福建閩侯人。文藝理論家。1962年從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任教於遼寧師范學院(今遼寧師范大學),曾任中文系主任。曾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理事。在《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等刊物上發表百余篇學術文章,著有《藝術創作規律論》《中西典型理論述評》等。
葉紀彬先生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界的拓荒者之一。在反思、創新的時代大潮中,他作為較早的思考者和開拓者,致力於將中國傳統文論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融會貫通。他撰寫的《藝術創作規律論》《中西典型理論述評》等著作,賦予文學本質論、文學典型論等傳統概念新內涵、新解釋,對中國文藝理論發展作出了承前啟后的重要貢獻。
關於“寫真實”與“寫本質”
在蘇聯文藝理論的影響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物質決定意識、內容決定形式的二元主義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界的主流文學觀。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中國文藝理論界也迎來學術反思、方法創新和體系重構的新時期,南北學人不約而同地開始對蘇聯文藝理論進行反思與批評,對中國古老的傳統文論進行爬梳整理,期冀在反思基礎上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藝術理論。
葉紀彬先生參與了文藝理論界最早的一場大規模自我反思,那就是關於文學“寫真實”與“寫本質”的論爭。按照魯樞元的說法,“寫本質”與“寫真實”之爭是新時期文藝理論界反思本質主義的一次較早、也較為重要的學術爭鳴,這次論爭既是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活動和文學性質的重新認知,也為新時期學術界對文學性質的重構奠定了基礎。這場論爭由王春元先生在《文學評論》雜志1979年第5期上發表的《關於寫英雄人物理論問題的探討》引發,該文提出“我們的文學不需要那種用理想化的方法或‘寫本質’的方法,去塑造‘完美無缺’的非現實主義的抽象的‘英雄人物’”。部分學人同王春元進行商榷,大量學者隨即撰文參與討論,葉紀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葉紀彬先生在《論“寫真實”與“寫本質”》(載《文學評論》,1982年第6期)一文中,贊同王春元的文學觀,認為這符合文學創作實踐,不同意學界個別人對王春元的批評。他在文中不僅沒有否定“寫本質”的意義,而且承認文學的本質及其背后的藝術規律。他對“寫本質”這一概念重新進行解釋,厘清“寫本質”的源流和演變:“寫本質”最初是為了實現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的結合,促使文學藝術更好地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狀況,“但由於‘寫本質’這一創作理論本身就是‘左’的文藝思潮與理論影響下的產物,因此造成這一創作理論本身的不科學,違背藝術規律,遠離關於文學藝術的正確命題”。在“不科學”的理論指引下進行創作,自然會對文學藝術產生負面影響,使得文學創作脫離實際。在葉先生看來,文學對現實生活的描寫恰恰是其本質屬性的體現,文學是無法描繪所謂的本質的,文學的真實性源自看得見的現實生活而非看不見的本質。對於真實生活的反映既是文學的基本功能,也是文學的基本性質,“寫真實”與“寫本質”並不可分,“寫真實”恰恰是文學對真實世界客觀規律的反映。
魯樞元等學者撰寫的《新時期40年文學理論與批評發展史》(2018年)一書認為,葉紀彬先生的《論“寫真實”和“寫本質”》在這次中國文藝理論界的大反思中,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質量的重要論文。葉先生的觀點對於學界重新梳理傳統文學觀和確立新的、更為全面的文學觀具有重要作用。
關於思想形象化與藝術典型
關於“思想形象化”的討論,雖然參與人數不多,但是影響甚大。正是這次討論,進一步推動了葉紀彬先生對文學創作規律的研究。
1986年,針對學界有關文藝結構、分類的認識,王元化先生在《文匯報》發表文章《關於目前文學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隨后《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1987年第1期《文藝研究》又刊發了他的《關於文藝學問題的一封信》。王元化先生認為,把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當作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開山之祖和基本觀點並不妥當,普列漢諾夫在論述托爾斯泰藝術論時,給藝術所作的定義,不能視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斷言藝術不僅是感情交往的手段,而且是思想交往的手段,並不見得比托爾斯泰的定義更准確。托爾斯泰並不是認為藝術不表現思想、內容,他的意思其實是說在藝術中思想內容是通過感性形態而表現的。這樣,藝術不是訴諸思考,而是發揮入人速、感人深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此后,李准、丁振海在1987年第3期《文藝研究》發表了《關於文藝學討論中的兩個問題》一文,對王元化先生的觀點表示質疑。
緊接著,葉紀彬先生在1987年第6期《文藝研究》發表長文《思想形象化非藝術的審美本質——參與有關托爾斯泰藝術定義問題的論爭》。在這篇文章中,葉先生詳細闡述了托爾斯泰以及普列漢諾夫等相關概念、思想的來源,同意和支持王元化的觀點,認為“思想形象化”非但不是藝術的審美本質,而且是與藝術的審美本質相抵牾的。把藝術創作過程斷定為“思想形象化”,其實質是主觀唯心主義創作傾向的表現,這種理論勢必導致在藝術領域內把藝術形象單純地當作演繹、圖解某種思想觀念的工具與手段。他贊同王元化先生在《文學沉思錄》中的觀點,認為“在全部創作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游離於形象之外從概念出發進行構思的階段。因此,由一般到個別的認識功能,不是孤立地單獨出現,而是滲透在由個別到一般的過程中,它成為指導作家認識個別的引線或指針”。
對於此次論爭,王元化先生極為看重,在他的《傳統與反傳統》《思辨發微》等文章以及日記中都有所提及。這場學術論爭也開啟了葉紀彬先生與王元化先生的友誼。1989年2月,王元化先生寫道:“同年(1987年)《文藝研究》第6期發表了葉紀彬先生《思想形象化非藝術的審美本質》的長篇論文……我在信中寫得很簡單,葉紀彬作了充分的發揮,論述詳贍。讀者倘要了解這場小小的爭論,請參考上述文章。”(王元化著《傳統與反傳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除深度參與時代大潮中的文學反思與爭鳴之外,葉紀彬先生最具開拓性的理論貢獻,是對於文藝創作規律的系統化研究,成果集成於由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藝術創作規律論》之中。在這部專著裡,葉紀彬先生用文藝學和美學研究方法,以藝術的審美本質為核心理論命題,將宏觀理論闡釋和微觀藝術解析有機結合,精辟而全面地論証了藝術創作的諸種規律。該書還運用心理學的相關概念,重新闡釋了形象思維——這一藝術創作的邏輯起點﹔用長達15萬字的篇幅,系統論述了藝術反映論的特征,探討了藝術創作過程中的“變形”“模糊”等基本規律,做到了宏觀的文學理論概括與微觀的藝術分析在理論層面上的結合,藝術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在審美研究上的結合,歷史唯物主義與現代心理學的結合。他將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論融會貫通,對藝術典型、意境、形象思維等文學基本理論概念進行新的解釋。這部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藝術創作規律的著作,其開拓性與原創性毋庸置疑。徐中玉先生在該書序言中說:“書內每能針對舊說,獨陳新意。”
1993年出版的《中西典型理論述評》,是在《藝術創作規律論》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該書上編是“歐洲典型理論歷史發展述評”,以典型類型說、典型特征說、典型個性共性統一說等三種主要理論傾向展開,有重點地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包括亞裡士多德、康德、歌德、黑格爾等,對不同學術傾向及其理論家的個性觀點做出較為系統、全面、深入的理論總結、概括與述評,從古希臘典型理論到馬克思主義典型理論都有所涉及。該書下編是“中國典型理論歷史發展述評”,採用重點評述的方法,闡釋了中國古代人物類型理論和明清之際人物性格理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關典型理論的觀點,他側重評述周揚與胡風、何其芳與李希凡等學者對於“典型”的論爭。對於中國典型理論的歷史發展,力圖做到“史、論、評”的三位一體。葉紀彬先生通過中西結合、古今貫通的方法對藝術典型這樣一個古老命題進行研究,這種開拓性的探索,迄今為止尚少有人問津。
一個人的研究生課堂
葉紀彬先生出生在福建閩侯一個大家族。少年聰慧的他,195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深得徐中玉教授等華師大老一代學者的賞識,1962年畢業后分配至遼寧師范大學(當時為遼寧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
在遼寧師范大學工作了一輩子,葉紀彬先生在理論研究之外,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教書育人之中。為提升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水平,他堪稱嘔心瀝血。
葉紀彬先生最初講授“文學作品選讀”“文學寫作”等課。“文革”期間,他被安排講授“文藝理論”課,借機深入研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述。“文革”之后,全國教育走上正軌,他在大學課堂開設“文藝理論”選修課,將一些基本概念、理論講授得十分清楚、明白,深受1977年、1978年入學的大學生歡迎。不久前,還有當年聽過他“文藝理論”課的學生,撰文回憶自己如何得益於葉紀彬先生——因為葉先生在大學選修課上把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與文學藝術發展不平衡一說講授得十分清楚,他得以順利考上研究生。
1989年5月,為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學科設立博士學位點一事,葉先生帶著筆者專程赴滬拜見王元化、蔣孔陽,爭取這兩位教育部學科評議委員的支持。對於這件往事,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遺憾的是,因為當時遼寧師范大學相關支撐學科實力不足,葉先生未能如願。
葉紀彬先生自1985年開始帶研究生,先后培養了近20名碩士研究生,其中不少人繼續完成博士學業,如今這些學生都成為各自領域的骨干、專家。葉先生沒有門派和學派之見,以開放式、包容式的態度讓學生自由發展,鼓勵學生博採眾長。對於青年學生對傳統文藝理論(包括對自己學術觀點)的質疑,他從不打壓或排斥,而是循循善誘予以鼓勵和支持,與學生就相關學術理論、觀點進行平等自由的討論交流,既為青年后學樹立學術研究上的自信心,也無形中培養了他們的創造力。1989年進入葉紀彬先生門下的黃丹麾回憶,他當時血氣方剛,經常與先生爭論,迄今仍然記得關於兩個問題的爭論:一是文藝是否為審美意識形態,二是傳統文藝學是否要引入西方文藝理論體系。這兩方面內容與葉先生的學術體系有很大差異,但是葉先生非常寬宏、包容,沒有簡單地予以否定,反而鼓勵黃丹麾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研究。黃丹麾撰寫的碩士學位畢業論文《中介思維與文藝闡釋》借鑒了德裡達的中介思想,發表后引起學界關注。正是由於先生的大力支持,黃丹麾的學術個性得以張揚,並最終成為中國美術理論界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
在教授青年學生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葉紀彬先生踐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理念,著力教授學生方法論。目前在國際關系學院任教的王慧玉教授,還記得當年考取葉紀彬先生研究生之后,初次見面,葉先生給她開的書單之長,令她震驚,其中既有從亞裡士多德的《詩學》、康德的《判斷力批判》、黑格爾的《美學》、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也包括俄國形式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接受美學等領域的專著。對於這些書,王慧玉開始閱讀的時候常讀不懂,隻能囫圇吞棗地硬讀。但是堅持讀下來,她的學術眼界得到極大拓展。她認為,自己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上之所以能夠具備一定的理論視野和學術深度,就受益於跟隨葉紀彬先生讀書這一時期的理論修養。
葉紀彬先生對學生悉心指導,以最大的耐心鼓舞每一位青年學者的成長,自己卻甘居幕后。張玉閣1986年開始跟隨葉紀彬先生讀研究生,他記得,自己發表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從立意、觀點到邏輯、論証都由葉紀彬先生親自指導、修改。但論文發表時,葉紀彬先生堅持拒絕署名,這令張玉閣十分感動。
筆者於1987年進入葉紀彬先生門下,就讀文藝學文藝美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當年研究生的招生數量少,葉先生隻帶我一個研究生,經常在家裡給我上課。雖然隻給我一個人上課,但他總是在書房的寫字台前正襟危坐。上課前,他家書房的沙發罩會整理得整整齊齊的,茶幾上永遠泡著一壺熱茶。那個時候我年輕氣盛,葉老師講課時我總是插話,后來,葉老師就改為自己先講一段,然后問我有什麼意見。我們的課堂由此就變成了討論課。剛開始時,我還拿著筆記本,記下先生講授的內容,后來就是拿著自己讀過的書與先生進行辯論。記得有一次我是拿著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原理》一書去上課的,葉老師翻看著書本上我畫的一道道筆跡,抬頭看了我一眼,然后點燃一支香煙抽了起來,邊抽煙邊與我進行討論。在我跟隨他讀書的三年裡,從來沒有被批評過一句。葉先生就是這樣寬以待人。
一個人的研究生課堂,對於筆者而言,早已習以為常。直到有一天,我准備課后外出,就帶著女朋友同去葉老師家。課后,她十分奇怪地問我:“葉老師給你一個人上課,還在書房打上領帶?”時至今日,當年的女朋友已是我的結發妻子,隻要是說起先生,她就會提起這一段。
一個人的研究生課堂,體現的是先生在傳道授業過程中的嚴謹與真誠。正是在葉先生的循循善誘與悉心指導之下,在他學術風范的熏陶之下,受教於葉紀彬先生的幾代青年人均在不同崗位作出了自己的成績。
由於常常在先生的書房裡上課,筆者對於他的書房頗為熟悉,印象最深的是長年挂著的一副對聯“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是先生自己的手書,清秀俊逸。后來,這副對聯換成了鄭板橋的詩“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不用說,這兩副對聯是先生一生治學、為人的格言。
葉先生的出生地福建閩侯,誕生過眾多知名學者,這個鐘靈毓秀之地經常成為我們學術討論之后的話題。有一次我問葉先生,大連與福州之間的不同是什麼?想不到他的回答竟是,“大連的氣候可以讓人一年四季安心寫作”。葉先生一生治學勤奮、努力拼搏,這在全校是出名的。我常常聽與葉先生同住在一個家屬區的老師談起:“葉紀彬老師家的書房燈光,黑得最晚、亮得最早。”葉先生稟賦南方山水之靈,同時兼具北方的開闊博大,再加上治學勤奮、嚴謹認真,才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界一位承前啟后的著名學者。
無論是參與“寫真實”“寫本質”“思想形象化”的爭鳴與討論,還是撰寫《藝術創作規律論》和《中西典型理論述評》,葉先生都是從文學基本理論層面進行正本清源,正如一股清流突破層層阻隔,恢復文學滋潤人類心靈生活的本來樣貌。葉先生喜歡用“荊溪”做自己的筆名,他的家鄉閩侯有荊溪鎮,江蘇亦有一水名曰荊溪。楊萬裡有詩雲“別是荊溪煙雨圖”,如果我們顧名思義,把此處的“荊溪”理解為荊棘叢中汩汩而流的溪水,這不正是葉紀彬先生學術人生的寫照嗎?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