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群,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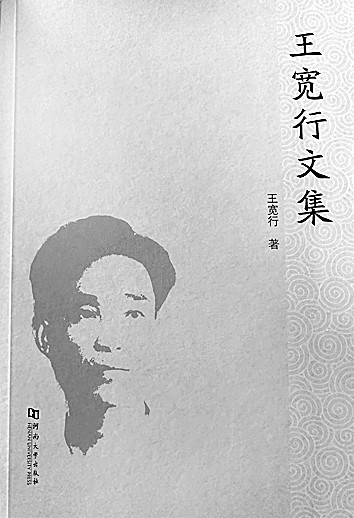
作者供圖

王寬行(右一)與友人在一起,左一為張如法。作者供圖
【述往】
學人小傳
王寬行,1924年出生,2004年去世,江蘇邳縣(今邳州市)人。1948年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休學,1950年9月到1952年7月在無錫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學習,1952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本科,畢業后分配到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今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著有《王寬行文集》。
一
1965年高中畢業時,我報考了清華大學土木建筑專業,可考前學校分別召集不同家庭出身的畢業生開會布置報考志願的消息,讓我有了不祥之感。果然,雖然我的成績完全合格,最終卻落榜了。
1977年,停頓多年的高考恢復了,對一直心心念念想上大學的我來說,真是一次歷史性機遇,然而,我隻能無奈再度止步:未能報上名。1977年高考隻允許1966、1967、19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報考,如我這樣1965年參加過高考未被錄取的考生是不允許報名的。不久后,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考研的年齡上限放寬了,而且對於有專業特長和研究才能的在職職工,報考時不受學歷限制。我馬上明白,這是我讀大學的唯一機會了!作為理工男的我,立即自學大學文科課程參加考研,原因很簡單,自學理工科無異於“自殺”。
1979年9月,34歲的我,歷經了14年小學、中學教書生涯后,考上了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即今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師從王寬行先生,成為寬行師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
面試時第一次見到濃眉大眼、心直口快的寬行師,他爽朗的笑聲時時回響在嚴肅的復試場上。看得出,在座的高文教授(1908—2000年)、華鐘彥教授(1906—1988年)等老一代學者都非常欣賞寬行師。面試時,華先生問我:荀子是法家還是儒家?為什麼?我回答完后,華先生做了點評。寬行師和華先生為此題還有一場小小的辯論,讓嚴肅的考場一下子變得活躍起來。畢業留校后,我參加過多次研究生面試,罕見此種景象。
后來我才知道,寬行師新中國成立前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專”)。無錫國專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張亮麗的名片,“培養的學生絕對數量不多,但卻保持了極高的成才率”,有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史的學者將其與北京大學等名校並稱。1953年寬行師畢業時,該校已改名為“江蘇師范學院”,他由江蘇師院分配到開封師院工作。寬行師和系裡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關系如此融洽,是因為寬行師學問扎實、見解獨到而又為人耿直,為中文系的老先生們所認可。
第二次見到寬行師已是開學后,地點是寬行師的家,校內排房中的一間(那些排房現在已經拆除,改建為河南大學開封明倫校區音樂學院、美術學院)。當時開封師院中文系許多老師都住在這些平房裡。盡管我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寬行師家的簡陋仍然令我大為吃驚:全部家當隻有一張單人床,一張破舊的三斗桌,幾個小書架和一些放在地上的炊具。
我沒有在開封師院讀過本科,可我對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並不陌生。1974年到1976年的這三年,我一直在開封師院歷史系“工作”。那時,開封空分設備廠“工人理論組”和開封師院歷史系共同承擔《王安石詩文選注》的工作,我是空分廠“工人理論組”向空分廠中學借調的高中語文教師。因此,我隔三岔五地要從歷史系去開封師院的教授院(河南大學金明校區南門外教授院,現已拆除)拜訪中文系高文教授,請他審閱我撰寫的初稿。與教授院的住房相比,寬行師的住所實在是太簡陋了。這種簡陋不僅表現在房屋的面積和結構上,而且表現在室內的家具上。
作為青年教師,寬行師與當時的開封師院教授相比,工資待遇相差懸殊。加上師母為農村戶口,孩子均在農村,經濟的重擔讓像寬行師這樣“一頭沉”(特指夫人系農村戶口者)的高校教師經濟一直很拮據,甚至負債累累。
寬行師一人獨居開封26年,直到1979年,師母和小兒子才辦完“農轉非”(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來到寬行師身邊,實現了家庭的初步團聚,當年的青年教師已成了年近六旬的老人。他的長子1978年考上徐州師范學院,畢業后進入邳縣縣中教書,直至退休。次子1982年到商丘一所中學當老師,后調入河南大學圖書館。唯一的女兒,因為已婚嫁,不能再辦“農轉非”,一直留在江蘇農村。
師母和小兒子的到來,給寬行師的生活帶來了不少歡樂。伴隨著師母的到來,20世紀80年代,寬行師告別了平房,搬進了今河南大學明倫校區西門外的家屬樓,直到仙逝。在今天看來,寬行師的新居既不寬敞也不豪華,書房仍然隻有幾個簡陋的小書架,一張結實無華的三斗桌,以及一把修補了多次的舊藤椅。我每次到寬行師家中問學,他都是坐在那把破舊的藤椅上談笑風生。
寬行師的穿戴也相當簡單,一套灰色的中山裝是他的標配。從我入校至寬行師去世的25年,他一直穿著同樣顏色、同樣款式的中山裝,無論在家中,還是在課堂上。作為長子,寬行師要照顧在老家的兩個弟弟,作為丈夫和父親,寬行師要負擔妻子和三男一女的生活,因此他自奉甚儉,常年不添置新衣。據說寬行師曾訂做過一套米黃色的中山裝,隻有出席重要會議或拜訪前輩、親友時才舍得穿。
寬行師的忘年交、河南大學文學院張如法教授在他個人博客上寫道:“‘文革’前畢業的開封師院中文系學生,回憶在母校的學習生活時,都要贊美寬行兄講課的魅力。如曾任河南省作協副主席、河南省文學院院長的孫蓀(孫廣舉)在《河南大學學報》上撰文說,王寬行老師講課氣勢恢宏、情感激越。‘文革’后七八十年代的學生,也對寬行兄的講課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就是先旁聽寬行兄的講課,心生敬慕之情,最終下決心考上中文系的。”張如法教授還摘錄了那篇文章的片段:“我待了一星期,一天不落地聽課,真是大開了眼界。印象極深的是王寬行老師講《孔雀東南飛》,開篇兩句‘孔雀東南飛,五裡一徘徊’,講了兩個學時,深入淺出、旁征博引:一唱一詠,手舞足蹈﹔輕音時,地可聽針﹔豪唱時,晴空霹靂。你的思緒被他調遣,時而泣,繼而涕,時而樂,繼而笑,時而探首側耳聽山泉叮咚,繼而仰天排胸嘯大江東去,那是一場難忘的藝術享受。可惜好景不長,第二天,我便要返鄉了。我萌生了強烈的上大學的念頭。”
二
住得簡陋,穿得簡單,但是,寬行師卻有著一顆“精致的大腦”。這顆“精致的大腦”以善於深刻的分析著稱於學界。他是開封師院中文系著名的雄辯家,講課、發言一向以深刻著稱。
在我三年讀研期間,寬行師給我講《史記》,講漢魏六朝樂府,講《論語》《孟子》,講唐詩。特別是一些名家名篇,寬行師講起來聲如洪鐘,每每拍案而起。屋中隻有我們師生二人,寬行師講課的氣勢、聲音,絲毫沒有因為隻有我一個人聽課而與他面對數百學生時有任何差別,大氣磅礡,揮洒自如,激情四射。
張如法教授曾寫過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記述寬行師講課時的情境,他(指寬行師)往往“先在黑板上簡要寫出兩種觀點讓同學思考,然后用粉筆在第一種觀點上打個大×。那時課堂上允許抽煙,他又有煙癮,便掏出香煙點上一支猛吸一口,嗵、嗵、嗵,從講台下來直走到教室后邊,又折回來,嗵、嗵、嗵,登上講台,拿起粉筆在第二種觀點上一邊打×,一邊高聲說道:‘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同學們顯出驚訝的神色,他於是非常自信地說道:請聽聽我的正確觀點和具體解析。”
寬行師做研究和他講課一樣,非常看重細讀文本。一次談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詩中“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頌詩書”,寬行師告訴我:一定不能理解成為這是寫劉蘭芝能干!這是寫封建禮教的教育!下文寫蘭芝回家,劉母的“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就將“十六頌詩書”改為“十六知禮儀”,可見,“頌詩書”是為了“知禮儀”。寬行師此類耳提面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寬行師給我講《史記·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時,對《鴻門宴》開篇的“項王大怒”中“大怒”二字非常感興趣。他認為:“大怒”二字表現了項羽的政治幼稚,表現了項羽入關后沒有認識到劉邦已經由昔日戰友演變為今日對手的重大轉折。因此,項羽的政治幼稚成為解讀《鴻門宴》的一把金鑰匙。我在《百家講壇》講項羽,主要講了項羽失敗的三大原因——政治幼稚、軍事被動、性格缺陷。這些認識都是我在寬行師“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在自己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漸清晰起來的。
再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寬行師非常看重“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兩句。他認為:“世”是什麼樣的“世”,“我”是什麼樣的“我”,“世”與“我”如何“相違”,這是解讀陶淵明歸隱的關鍵。講清楚了這兩句,整個陶淵明的歸隱就迎刃而解了。
可見,寬行師具有文本解讀的非凡功力。這種功力不局限於解讀文本,而且還能夠通過解讀文本解讀作家。這是寬行師的獨門絕活!細讀文本,成了我此后數十年教學和研究的基本功,也成就了我在研究中的多項重要發現。
三
寬行師最鐘愛的研究課題有兩個:一個是陶淵明研究,另一個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寬行師見解深刻的特點在他的陶淵明研究中表現得非常突出,而且寬行師的研究興趣,讓他很快就有了參與全國陶淵明研究的機會。
新中國成立后,陶淵明研究一直存在較大分歧。
1953年,著名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李長之撰寫的《陶淵明傳論》出版。此書力主陶淵明受曾祖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響,並不尊崇東晉王朝,“反映了沒落的士族意識”。
1954年,閻簡弼撰寫文章《讀〈陶淵明傳論〉》,批駁李長之對陶淵明的指責和否定,基本肯定陶淵明傾向人民,和人民的願望相一致。
多數專家肯定陶淵明的積極一面,認為他“躬耕自資”,侍弄桑麻禾黍,不為五斗米向鄉裡小兒折腰,與農民有深厚情感,在老庄思想和隱逸風氣盛行的晉代,殊為難得。
1958年,陳翔鶴主編的《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組織了一場全國性的陶淵明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立即吸引了中國古代文學界眾多學者的高度關注。
這場討論始於1958年12月21日《文學遺產》第240期發表的3篇評陶文章,止於1960年1月3日第294期發表的1篇評陶文章,歷時一年余。討論結束后,《文學遺產》副刊選編了《陶淵明討論集》(以下簡稱《討論集》)作為總結,並由中華書局1961年5月出版。
《討論集·前言》介紹,從《文學遺產》第240期發表第一批討論文章起,至1960年3月底止,共收到有關陶淵明的討論文章251篇。入選《討論集》的有正文27篇,附錄3篇,計30篇。
在這30篇文章中,以個人名義發表的僅21篇。此21篇發表在《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者17篇,寄往《文學遺產》副刊未發表最終收入《討論集》者3篇,發表在其他刊物收入《討論集》者1篇。王寬行《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一文是未能在《文學遺產》副刊發表卻最終收入《討論集》的3篇論文之一。
寬行師撰寫此文時,36歲。在全國投稿的251篇文章中,能獲得出線權,特別是投稿時未刊載,最終能收入《討論集》,殊為不易。這一切皆緣於他對陶淵明深刻、獨到的見解,也表明他的見解在當時已處於時代的前沿。即使在今天,我重讀此文,仍然可以感受到內心的悸動。
寬行師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發表文章並非偶然。他1953年分配到開封師院,1954年便在《人民文學》3月號發表與權威商榷的文章《關於對〈詩經·將仲子〉一詩的看法》。在專業期刊極其稀缺、專家教授投稿亦不容易被採用的當時,寬行師的科研實力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張如法教授生前曾回憶他初識寬行師的一個細節:“我於1959年7月從華東師范大學畢業,8月被分配到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由於寬行兄在古代文學教研室,我在現代文學教研室,他又長我14歲,所以比較陌生。引起我對他注意的,是系裡為提高我們這批新教師的學識水平制定的一個系列講座。擔任導師的有李嘉言、華鐘彥、高文、萬曼等著名教授,后面赫然有一講師職稱者,此人就是王寬行。人皆有好奇心,我們一些外校畢業的新教師,聽說好些教授、副教授都不能為我們開講座,為何獨獨這位講師能名列導師其列?其是‘何方神仙’?有何‘法道’?經過打聽,這才知道王寬行的學術功力非凡。”
我們評價一位學人,往往有兩種模式:一是看他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認為級別越高的刊物,作者的水平就越高﹔二是看他的代表作處於什麼水平,達到什麼高度,這就是代表作評價制。兩種評價模式各有利弊。刊物級別高,不等於其所發表的文章都是最高水平文章,也不等於其作者都是最高水平的研究者。刊物和刊發的文章之間可能會有不完全協調之處。代表作評價制,是通過一位研究者的代表作,判斷他的實際研究能力和他的研究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以代表作評價制衡量寬行師的陶淵明研究,他可算是一位被學界長期低估的學者。
寬行師的陶淵明研究不僅有《討論集》收錄的《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還有收入他個人文集的《試論陶淵明的“質性自然”》《也談陶淵明的化遷思想與審美創造》《也談陶淵明的政治傾向》《談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這些評陶文章,如《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一樣,達到了那個時代評陶文章的較高水平。
在寬行師留下來的不多的遺作中,有5篇同樣具有很高水平的陶淵明研究文章,足以說明寬行師對陶淵明研究的鐘情。
寬行師的遺作篇數不多,特別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領域保留下來的文章甚少,這本是寬行師為研究生講得最多的話題,他自己極少寫成文章,而是毫無保留地講給了自己的研究生,不少觀點被他的學生寫成論文發表了。為什麼一位以雄辯著稱的先生著述不多呢?“述而不作”的觀點深刻地影響著寬行師那一代人。
寬行師遺作的一個特點是以解析作品為主。新中國成立后,河南大學的許多院系或獨立成校,或並入他校,自己則降格為開封師范學院。既然名為“師范學院”,培養中學教師便成了這所大學最重要的任務。中文系負責培養全省的中學語文教師,自然要給中學語文教師講中學教材,這種“生存狀況”導致了大量作品講析文章佔據了寬行師遺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解讀古詩文名篇最見文學史家的功力,幾乎所有名家都在這方面下過大功夫。北京大學葛曉音教授匯集北大名家林庚先生的多篇文章,選編為《詩的活力與新原質》一書(生活書店2022年版),其中專辟《談詩稿》一章,收錄了林庚先生講讀16篇作品的文章,如《君子於役》《易水歌》《青青河畔草》《步出城東門》《漫談庾信〈昭君辭應詔〉》《秦時明月漢時關》《談孟浩然〈過故人庄〉》等。這就不難理解寬行師的文集中為何有不少名作解讀的文章。
雖著述不豐,但成文極有分量,朴實無華的文字后面,難掩一代學人的風採。雖然,寬行師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獨到見解已經百不存一了,但是讀者從這些有限的存世之作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位獨具隻眼的學者的銳利眼光。這種眼光是永恆的,這就是寬行師學術生命的價值所在。學術永遠不以量取勝,代表性文章是體現一位學者真正價值的標志。
四
寬行師是一位尊師重道的長者,是一位具有文人風骨的學者。他和他的老師吳奔星先生、廖序東先生的友誼令人動容。
吳奔星、廖序東兩位先生是寬行師在無錫國專時的老師。吳先生是詩人兼學者,廖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廖序東先生與黃伯榮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是國內高校應用最廣的現代漢語教材。寬行師幾乎每年寒暑假回江蘇老家時,都要到徐州師范學院看望兩位老師。一次吃飯時,吳先生對寬行師說:“讓秉辰(寬行師長子,時在徐州師院中文系讀本科)過來一塊兒吃,來跟他吳伯伯說說話。”寬行師當即就說:“絕不能這樣稱呼!您是我的恩師,永遠不能變。”寬行師在無錫國專上學時,吳先生講授現代文學課。一次上課時,有學生要求吳先生講講《孟子》,吳先生對學生說:“若是講《孟子》,可以請王寬行講,有關《孟子》的學問是他的專長。”
一次,寬行師因有急事,回老家時路過徐州而未下車。吳先生再次見到寬行師責怪道:“我都奇了怪了,你工作在河南,家在邳縣,徐州是你飛過去的?”師生之間的眷眷深情流淌在吳奔星先生對寬行師的責問之中,讀之令人淚目。
吳奔星先生的兒子在張如法教授的博客上留言:“寬行先生尊師重道,我最有感受。他是家父在江蘇師范學院的老學生,年齡隻比家父小11歲,但每次來看望家父,都是畢恭畢敬,對我總是稱‘心海弟’。記得寬行先生最后一次到南京看望家父,是2000年,當時犬子上小學,家父讓他喊寬行先生‘爺爺’,寬行先生大聲說‘這怎麼行,這怎麼行!心海是小老弟,心海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子!’后來,寬行先生還專門給我兒子買了一支英雄牌的鋼筆。”“家父臥病后,寬行先生經常電話問安,前后有十多次。起初,父親還能夠接聽電話,聽到寬行先生的聲音,就很激動。在這裡,不能不提一句,曾經的很多座上客,在家父臥病后,就再沒有了音信,但寬行先生,基本是一個月打一次電話詢問病情。古人雲:學貴得師,亦貴得友。信乎!”
我留校后,寬行師經常到我家小坐,每次都要談到陶淵明研究,並邀請我和他一塊兒從事該項研究。由於我當時已有了自己的研究課題,隻能答應完成手中的課題后再和寬行師合作,可我的課題一個接一個,始終沒有來得及和寬行師合作進行陶淵明研究。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我去看他,他仍然興致勃勃地和我商討陶淵明研究,可惜我最終未能實現寬行師的願望。“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悲夫!
回首當年和寬行師促膝交談的時光,雖歷歷在目,但俱成往事,不勝噓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