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人小傳
鄭敏,1920年7月18日生於北京,祖籍福建閩侯。詩人,翻譯家,西方文藝理論家。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1952年於美國布朗大學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55年回國,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組(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60年到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任教。著有《詩集1942—1947》《尋覓集》《英美詩歌戲劇研究》《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等。1981年,鄭敏與王辛笛、曹辛之、穆旦、杜運燮、陳敬容等合出詩集《九葉集》,他們因此被稱為“九葉詩派”。

百歲生日當天的鄭敏 資料圖片

《九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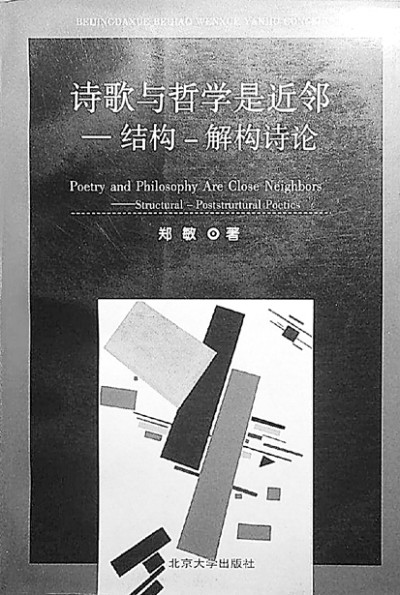
《詩歌與哲學是近鄰》
【大家】
7月18日,“九葉詩人最后一葉”鄭敏先生在清華大學荷清苑家中度過了百歲壽辰。
鄭敏是詩人,也是學人。她青年成名,詩作引燃了后來幾代詩人的靈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她的詩論開20世紀80年代風氣之先,將西方解構主義哲學引入對漢語文字、新詩創作、文學史觀和中華文化傳統的重新理解,在文藝理論領域引發深遠回響。她的百歲如同一本厚實的書,記載著她獨特的天賦才能、她不懈的創作實踐和求知努力,也刻寫著與我們民族命運相呼應的滄桑,有坎坷,也有堅毅不屈的進取。
鄭先生曾寫下詩句:
不能忘記它
雖然太陽已經下山了
山巒的長長的肢體
舒展地臥下
穿過穿不透的鐵甲
它回到我的意識裡
在那兒放出
隻有我看得見的光。(《心象組詩》之一)
那束引領她前行不倦的光,讓我們翻開詩人的歲月書卷去尋訪。
一
鄭敏的求學之路十分特別。她19歲通過西南聯大入學考試,被外文系錄取。報到注冊那天,她念及自己的哲學愛好,想到自修哲學比外國文學難,便果斷轉入哲學系,改修西方古典哲學。
大學三年級,在德文教授馮至的指點和鼓勵下,她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作。1947年,她的詩歌作品結集出版,收錄於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十輯,題為《詩集1942─1947》。此時,鄭敏不過27歲,儼然中國新詩界的一顆新星。
鄭敏的詩作從一開始便風格鮮明,被稱為“用清明的數學家的理智來寫詩的詩人”。詩人唐湜如此評述道:“她雖常不自覺地沉潛於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蕭然物外的觀賞態度,那種哲人的感喟卻常躍然而出,歌頌著至高的理性。”
情與理緊密交織並力求理智的超然和超越,這種美學追求脫胎於青年鄭敏的個性,離不開她的哲學底蘊,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它其實也是中國現代派新詩當時共同推崇的一種創作傾向。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裡爾克、艾略特、奧登為代表的歐美現代主義詩潮登陸中國。一批年輕詩人受其吸引,用心揣摩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經驗,將其應用於漢語新詩的藝術探索。他們的創作試驗各取一徑,白話詩的結構、修辭、表達手法在他們手上呈現出多種樣式的新發展。百花齊放的園地裡,青年鄭敏的詩作乃是其中一枝生機勃勃、散發幽香的蒼蘭。
繁榮於40年代的現代派新詩有別於此前的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取向的白話詩。它從中西詩歌藝術對話中提取靈感,嘗試超越單純的“我手寫我口”或“我手寫我心”,是中國現代漢語與當時的社會情景、人文思考以及詩歌特性的融匯和創造。用袁可嘉先生的話說,他們的詩是“新的綜合”的藝術,它“包含、解釋和反映了人生現實性”,同時“絕對肯定詩作為藝術時必須被尊重的詩的實質”。
然而,具有時代先鋒性的藝術實踐注定屬於小眾。在現代派筆下,“詩作為藝術的本質”常常體現為詩句艱深晦澀,詩意迂回、跳躍而多層,詩人們的嚴肅和深沉給讀者設置了智性門檻,不易親近。這種疏離大眾趣味的藝術立場顯然不能直接服務於抗日戰火和民族救亡。因此,在滾滾而來的革命洪流中,現代派新詩受到抨擊,被斥責為小資產階級情調。新中國成立后,它們被階級分析所主導的文學評價所否定和拋棄。
二
直到30多年過去,新時期開啟詩藝探索的新征程,40年代的現代派新詩才重新被挖掘出來,回到讀者的視野。1981年,《九葉集》出版,鄭敏已經61歲了。
對於九葉詩遭遇的挫折,鄭敏在90年代接受訪談時表達了深刻洞見。她認為,拋卻中國歷史的特殊進程帶來的具體文藝觀斗爭和恩怨糾葛,九葉詩派的歷史沉浮歸根結底體現了二元思維模式對我國文藝評價體系和文藝心態的束縛。例如:革命/藝術二元評價標准。40年代的“七月詩派”和“九葉詩派”原本題材互補、詩風相異,並不構成相互排斥和對抗的關系,然而,革命第一藝術第二的標准偏偏在兩者之間“引發了一場沒有意義的矛盾”。七月詩歌的語言和主題貼近底層,富於昂揚的戰斗精神,因而被新中國文學史教材樹立為模范,九葉詩講藝術,“不革命”,批評界就無法正視它在新詩發展史的位置和價值。再如:區分二元文化身份、貶此褒彼的時代思潮。九葉詩人普遍接受過高等人文教育,通曉外國語言文學,善於表達知識分子的敏感和沉思,被喻為中國現代的哈姆雷特﹔七月詩派擁抱“人民本位主義”,強調“集體的英雄主義”和扑向光明的行動性,被稱為武裝起來勇於搏擊的堂吉訶德。就精神價值而言,堂吉訶德的單純與哈姆雷特的復雜本是對立互補,堂吉訶德質朴的民間生活邏輯和樂觀主義情懷與哈姆雷特窮究事理的憂思各有其用。可是,如果將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簡單對立起來,哈姆雷特的危機意識和輾轉思考也就被掃蕩出局,無人傾聽也無足輕重了。
“大躍進”時期,鄭敏被下放到山西臨汾農村,由於長期飢餓和營養不良,全身浮腫。“四清”運動,她再到山西農村插隊,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一年。接著文革,歷史清查和開會批斗從天而降,她不得不將所有詩集付之一炬,不再談詩,直到浩劫結束。也就是說,即使不算個人遭受的委屈和創傷,從30多歲到50多歲,至少20年韶華在風雲變幻中流逝。詩歌沒有生命,不會為世道無常而痛苦,那麼詩人呢,是否惱恨時光虛擲,為遠離詩歌而遺憾?
鄭先生的冷靜和超然在詩歌內外始終保持一致。她說,這20年對於她是拿什麼都換不來的人生經驗。倘若不是下鄉與農民生活在一起,她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不會知道中國有那麼貧困的地方,不會了解如此貧窮的人們離文化知識多麼遙遠、過著怎樣的生活。與中國農民的忍辱負重相比,她所經歷的肉體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麼。而且,這段農村經歷,讓她從此忘不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衛和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因此,即使是在那個年代,她也總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視世相、積累思辨而不墜於悲觀絕望。
“真正的詩人總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給歷史的風暴”,這是鄭先生一片赤誠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膚的體驗才能讓她深刻地了解這個國家。她的無悔是真實的。
正因為關切民族歷史和民族利益甚於一己境遇,鄭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澆灌希望,能夠從哲學層面——二元認知論——來理解九葉詩派的歷史命運。也正因為痴迷於新的思考和求索,鄭敏先生無暇在改革開放后加入傷痕文學群體哀哭過往,相反,她猶如青春重返,飛奔向前,熱情擁抱新生活,投入新創作。
1979年,鄭敏在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開設英美文學和西方文學理論課程,同年發表《有你在我身邊——詩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學生命正式開啟。
三
鄭敏先生十分喜歡海德格爾的名言“詩歌與哲學是近鄰”,因為這句話恰當描述了她的心靈旅程。她一生在文學和哲學之間自由徜徉,得到了雙向滋養。
鄭敏在西南聯大主修西方哲學,而她1948年前往美國常青藤盟校布朗大學繼續學業時,又將研究轉回西方文學領域,以論文《約翰·多恩的愛情詩》獲得文學碩士學位。
1985年,著名美籍華人學者葉維廉邀請鄭敏赴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用英文講授中國現代詩歌。這是鄭敏自1955年留學歸國后頭回訪美。
30年,舊日的學生已成長為教授,曾經的青年已兩鬢染霜,可她對世界的好奇並未衰減半分。講學之余,她抓緊一切時間收集瀏覽60年代以后的英美詩歌,勤奮研讀正值黃金收獲期的當代歐美文學理論。
有沒有一種學理可以說清楚二元思維模式的起因,解除它帶來的禁錮,把我們對於詩歌藝術的認識、對於文化興衰的思考引向更深處?——這是鄭敏先生從半生坎坷中萌發的困惑,也是她回到詩壇和大學講壇后一直嘗試求解的學術問題。或許是偶然,也可以說是有心追問的必然結果,法國哲學家德裡達的解構主義論著適時出現,照亮了她的思考,解開了她長久的迷惑。那一刻仿佛她在詩裡所寫:
一隻手
點燃一盞燈
黑暗縮向角落……(《燈》)
四
亞裡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經驗的符號,書寫是口語的符號。”西方人自古相信,人類用聲音命名世間萬物,然后發明書寫符號把聲音記錄下來,因此,聲音比書寫離真實更近。這種語音中心主義信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又給予了補充和鞏固。依據舊約《創世紀》的記載,上帝一言創世,神言是宇宙的絕對開端。既然神言是神聖真理的載體,那麼,書寫模仿聲音,離真理遠一層,自然低一等。
到了20世紀初,法國語言學家索緒爾發現,語音和語義組成一個完整的語言符號,並不是什麼共同本質或真理屬性使兩者一一對應、相互綁定﹔真相僅僅是任一語音都與別不同,任一語義也與別不同,兩者任意搭配,約定俗成。也就是說,語言是一個完整自足的系統,其功能由符號內部以及符號之間的差異結構所決定,它並非神創,也不隨人的主觀意志轉移。
60年代,德裡達卻指出,完整封閉的符號結構並不成立,語言也並不是一個完整自足的符號系統,因為語音和語義之間所謂確定的一對一關系隻存在於假想之中,語音一旦發出,就會不斷自我分解,衍生差異,將意義向后推延。索緒爾認為,語言系統中的差異是靜態不變的,所以意義如同實體,確定無疑﹔德裡達則提出,差異在時間中生生不息,在空間裡不斷擴散,意義在這個過程中變化不息、永不釘死,語言才成其為語言。
德裡達認為,語言之源恰恰在於形成差異的力量、產生差異的活動和差異本身,語言的本質恰恰是意義不確定也不穩定,也就是一直被西方人輕視的“書寫”。口語和書寫的等級關系,在德裡達看來,代表著西方哲學范疇的普遍特點——一元為中心,居於主導地位,另一元在邏輯上和價值上處於低級地位,受前者支配和壓抑﹔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一元權威中心、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建筑在此地基上。而解構主義立場則與形而上學相對:時空、萬物永遠處於“書寫”也就是無形的、不可見卻無時無處不在的差異衍生運動中,一切中心蘊含著擦抹中心的力量。
解構主義雖然是20世紀的新事物,其觀念原型可上溯至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流變說,隻不過西方哲學對“存在”的信念和興趣壓倒一切,終使形而上學成為西方哲學主導體系。
德裡達對索緒爾語言哲學以及西方哲學史的革命性解讀,催生了解構主義學說。解構思想隨后擴散滲透至西方各人文學科,再啟發和衍生出多種改變世界的新理論,如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但在80年代,形而上學權威尚存,解構主義破舊布新之力雖然初顯,仍然是一種新鮮前衛的思想,即使在歐美,也有相當數量的人文學者不能予以正視。論年齒,鄭敏先生比德裡達還年長10歲。她年輕時所取法的西方現代主義詩潮高揚“客觀性”“智性”“非個人化”旗幟,何嘗不是崇拜超驗一元價值的形而上學論調?然而,年過65歲的她以驚人的敏銳領會了解構思想的學術意義和潛在價值,毫無困難地完成了知識、觀念和自我意識的更新。從80年代后期開始,她陸續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論文,將解構理論引入對當下中國新詩寫作、文學批評、文化傳統等現實問題的討論,成為解構主義中國之旅的開拓者。
五
文學生涯裡,鄭敏先生體會最深的,恐怕就是拘泥於非此即彼的二元對抗思維模式對新詩創作和批評的禁錮與傷害。改革開放前,把革命和藝術看作二元對立價值的文藝批評模式是一個例証,它導致許多優秀文學作品被簡化、扭曲解讀,最終被打入冷宮,也導致創作領域假大空盛行。改革開放以后,文壇興起的反崇高潮流也是一個例証。雖然后者源起於反思歷史、矯正僵化虛假文風的願望,但它試圖將崇高/卑微、高雅/低俗二元等級秩序顛倒過來,實際上不過是逆反心態的呈現。此外,9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寫作/口語化寫作、學院派/民間派紛爭迭起,新詩各流派的“創新”宣言無不力求與某個想象的“落后”標靶劃清界限,以示先鋒,在鄭敏先生看來,這裡的寫作心態仍然失之盲目,對文學創造力有害而無益。為此,她發表了《今天新詩應當追求什麼?》《中國新詩八十年反思》《時代與詩歌創作》等一系列文章,表明她對文壇現狀的關切,進而闡述她的解構主義創作主張:主觀/客觀、個人/群體、宏大題材/個人獨白、靈/肉、雅/俗並不是你死我活、東風壓倒西風的關系,它們相互依存,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相互轉化﹔切斷二者的聯系和對話,擇其一而敵視另一端,必使詩人目光短淺心胸狹隘,使詩歌喪失品質。
許多歷史上遭遇過不公和冤屈的文學知識分子,在平反后很容易投奔文學意識形態的另一極——既然極左是錯誤的,那麼越往右自然越正確﹔既然抹殺個人感性世界是錯誤的,那麼,私人經驗乃至感官感受自然高於一切,代表文學的天命。鄭敏先生卻始終保持冷靜,不為逆向的情緒所動,堅持強調“詩人的心靈與時代的聯系”。她在文章中指出,過去,整齊劃一的宏大主題要求和創作形式規范抹殺個性、壓制想象,固然對文學創作造成了致命打擊,但是,反過來,倘若以小小的個人天地為唯一創作核心,作品也不可避免會流於平庸和狹窄,因為“兩種相反的錯誤相互輪替並不能產生一個正確的至理”。
改變二元對抗思維,當然不僅僅是文學創作亟待解決的任務。鄭敏先生銘記著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再三撰文呼吁教育界和文化界突破新文化/舊文化、先進/落后等二元刻板認知,把中國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設引向健康道路。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鄭敏先生迅速覺察到伴隨著歐美強勢地位的“全球一體化”對於地球多元生態的侵蝕和壓制。在她周邊,她發現:
在幾代中青年國民和文化精英中間,“傳統”二字已意味著保守落后,傳統文化在集體潛意識中等同於現代化的對立面。一種隱在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正隨著現代化的追求在中青年中悄悄地蔓延著。(《全球化與文化傳統的復興》)
在鄭先生看來,國人的文化自卑感和西方中心主義,是我們“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隻停留在五四時期”、許多要緊的認識尚沒有走出“新文化運動”歷史階段的表現。(《教育與跨學科思維》)我們沒能從20世紀初激進的自我批判和自省中走出來,進一步深化自我認識,故而陷入“新殖民主義”,故而輕易被西方設置的“現代文明/落后民族”等二元對立觀念所俘虜,成為馴服的信徒:
所謂的“新殖民主義”可怕之處就在於它不是如老殖民主義那樣以佔領土地為目標,而是從經濟利益出發,以商業文化潛移默化地改變一個民族的生活倫理價值觀,使他們遺忘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智慧,淪為強權國的文化殖民地……而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地解放落后民族,賜給他們現代文明的口號下進行的。(《歷史時刻:中華文化傳統的復興與教育改革》)
鄭先生認為,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並相信“文化傳統與先鋒並非二元對抗”,才能確保我們民族在精神層面的獨立選擇。(《對21世紀中華文化建設的期待》)同時,我們必須挖掘自己幾千年的古老文化智慧,向中國文化傳統取經,賦予其符合時代精神的新闡釋,才能抵抗“文化審美與追求受到消費市場的宣傳操縱”,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在物質豐富與精神境界間的平衡》)
六
假如今天有人回顧“解構主義在中國”的旅行和本土化發展,鄭敏應該是關鍵的一個點,誰也繞不過去。然而,實際上,她恐怕又是最容易被學術史專家遺忘的人物。
她一生不合潮流,不通時務。青年時代,她對“先鋒藝術”著迷,與時代的革命主旋律擦肩而過。暮年,趕上全球化浪潮,當文壇和學界以追隨西方時尚為榮的時候,她又率先“潑冷水”,借西方之矛——解構主義——反西方中心主義。她不憚其煩,撰文倡導從古典漢語文學和中華傳統文化吸取現代性營養,闡述其對於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建構民族文化身份、重樹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以致被外國文學批評界同行譏為“新保守主義者”。
當然,這個外號鄭敏先生置之一笑,並不在乎。從70年代末回到工作崗位起,她專心教學、研究和寫作,一直與學科權力、學術名利保持禮貌的距離。80年代,她被授予“九葉詩人”桂冠,名氣暴漲。緊接著,她的解構研究和文化批評文章引發巨大反響,在文藝理論界聲名鵲起。但她始終習慣獨來獨往,既不參與課題經費的角逐,也不謀求學術組織或學術圈的認可。對此,人們常常說她清高傲世。其實,她僅僅是覺得時間寶貴,不容務虛和浪費。
不浪費時間空談,既是鄭敏先生不明言的學術准則,也是她的教學准則。1986年,她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指導博士研究生。從那時至今,她與學生一直保持著最純粹的學術交流關系。
她仿佛理性的化身。指導論文的時候,她思維敏捷,邏輯嚴密。她的連環反問殺傷力強大,常常將准備不足的學生逼入絕境而迫使他不得不加倍用功。上課,課下交流,她幾乎不談自己的私事,也不怎麼過問弟子們的私生活。她從不沉溺於個人過往的得失而感懷念舊,好像沒有念念不忘的得意功績,也沒有耿耿於懷的哀愁怨恨。她的興趣和話匣子總是面對當下的公共領域,話題可以是任意一條閱讀感受、學術隨想、時事新聞、國際事件,也可以是由此延伸開的宏觀論題——文學、藝術、文化、教育、民族素質、國家道路。討論的時候,她總是開朗、愉快的,時而滔滔不絕,時而充滿好奇和期待地探究年輕人的想法、與學生平等地辯論。
她永遠平和、開放,身上沒有老人的暮氣專斷,沒有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多我什麼都懂,沒有過去的時光多麼美好曾經的世界多麼完美可惜你們沒趕上,沒有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老了沒關系你們未來怎麼辦……她總是對每個新日子每個新現象感覺新鮮,渴望求索新知。對於她的學生們,這些正是她最具感召力和魅力之處,也是她影響最大而讓人渾然不覺的東西。
鄭敏先生指導博士生17年。在她的垂范下,師生同窗之間沒有基於利益的往來,沒有相互關照、一體共榮的私交。除了偶爾相約交流一下學術興趣,多數時間,大家彼此相忘於江湖。相聚也好,相忘也罷,鄭先生均視為自然。鄭先生再三明確表示,她不歡迎學生無事登門請安。她總是說:“逢年過節,來往應酬,說些無關痛痒的話,最沒意思了﹔你要來,就帶著問題來,我們一起討論。”正因為如此,數十載師生情滲透入靈魂深處,各人卻依然是彼此尊敬的個體,沒有形成所謂“師門”。
從世俗的眼光看,鄭敏先生這些做派似乎過於嚴肅,有點不近人情。可是,隻要靠近她的心靈,你就能感受她的溫柔和情趣,被她吸引。她的客廳牆上,挂著淡雅的水彩畫和素描。她的家具老舊朴素而整潔,櫥櫃和台面上總有朋友送來或自己種植的鮮花靜靜盛放。客人到來,茶幾上永遠提前備好了香茗、杯碟和各色小點心,學生來上課也是如此,因此,無論訪客進門前多麼忐忑,坐下的一刻便放鬆了。
不管是電話裡還是面對面,她聲音柔和、甜美,字字清晰,語句永遠自然流暢、從容不迫,有時說著說著自己先笑起來,笑聲帶著一貫的自信和果斷。她的聲音溫柔而有力,仿佛智慧和意志滲透於每個語詞,讓人自然而然感受到分量。
她熱愛古典音樂,留學美國期間曾經跟隨老師學習三年聲樂。不過,她從來不顯擺這段歷史,不在這個話題上高談闊論。音樂起時,她合上眼帘靜靜聆聽。過后,或許和同伴簡短地交談一兩句,你可以從她臉上看出悠遠的深思和心魂的沉浸。
鄭敏先生在《貝多芬的尋找》一詩中寫道:
用什麼能擁抱億萬人們?/伸出多瑙河的手臂/點燃北斗的眼睛/用像海蚌一樣開合的堅硬的嘴唇/申訴他對人們的愛,對黑暗的恨……
鄭先生和貝多芬一樣,愛智慧,愛真理,愛人。她把愛寫在詩歌中,論文中,正如貝多芬把他的愛寫在交響曲中,耳聾也阻擋不住。這就是我們在百歲詩人鄭敏的人生日歷中找到的光。
(作者:蕭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