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
編者按: 近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階段性成果——“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隆重推出,把《系年》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系年》是清華簡的一部分,是一部完整的、未見記載的先秦史書,無論是從史料學還是史學史上,都是十分重大的發現。作為一部兩千多年前的史書,《系年》給我們的新知是大量的,如何理解這部史書,還需要廣大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本期專刊特邀請3位專家學者撰文,以商學界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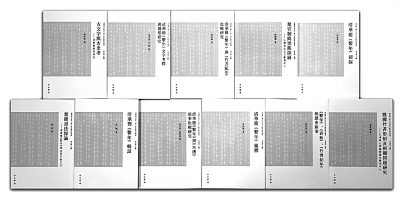
“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書影 資料圖片
清華簡是戰國楚簡,多達2496枚,大部分是完簡,字跡清晰,形式多樣,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史類文獻篇目雖然不是很多,但史料價值非常高。在史類文獻中有一篇記自西周初年,迄至戰國早期的完整史書,就是《系年》。經過將近5年的努力,近日,前期成果“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問世。作為主編,在此介紹一些基本情況,談一點個人想法。
出土文獻與傳統文化
傳統,尤其是優秀的傳統文化,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大問題。傳統文化在歷史上斷斷續續,起起伏伏,但大都與國家的強盛與否相關。為了國家的強盛,常常反對傳統文化,歷史上的秦與新文化運動皆如此﹔國家一旦強盛,就會倡導傳統文化,歷史上的漢與現今亦如此。
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上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斷裂。歷史記載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末戰亂造成的思想禁錮與文獻散失。我們今天的學術根基是漢代人搜羅殘余構建起來的。漢惠帝除挾書令,其后逐漸開始對文獻搜羅、整理、研究,到了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等把當時所見的圖書做了全面的清理,劉歆在《七略》中分類介紹,也就是《藝文志》的前身。漢代的學術,一直是以文獻的整理與闡發為核心展開的。隨著先秦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我們對這個過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第一,先秦古書很多,但留存到漢代的很有限。《上博簡》《清華簡》中的大部分古書《藝文志》未著錄,也就是說,這些書漢代人沒見過、也沒聽說過。
第二,秦朝的禁書令很有效。最近陳偉先生主編的集成性巨著《秦簡牘合集》出版,其中除了個別記錄鬼怪故事的木牘外,沒有古書。
第三,漢代學者見到一部分“古文”文獻,有金文銘刻也有簡書,像張敞這樣的好古之輩還能夠釋讀。這些古文文獻在當時就成軒然大波,引發經久不衰的今古文之爭。我們可以理解,當時,一部分官方學閥,依照其所見材料構建起一套學術體系而獲得不可動搖的地位,突然出現的新材料否定了其慘淡經營的學術體系,動搖了其學術地位,情何以堪?不承認,進而誣說是假的,在歷史上每次重大發現之后,都會有這樣的人出現。“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漢代一部分人面對出土文獻就是這麼做的,這也可以說是另類“傳統”。當然,對以牟利為目的的假簡需除惡務必盡,我們堅決支持。
第四,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所有傳世先秦古書都經過漢隸的轉寫,先秦古本的真實面貌已經完全不可知了。
第五,漢代人所見有限的先秦古書,現在絕大部分也佚失了。
這也就是說,漢代雖然在秦火余燼基礎上“復興”了文化傳統,但先秦時代的很多文獻,漢代人已經見不到了﹔漢代人所能見到的,很多我們已經見不到了﹔我們的早期學術傳統就是在這樣有限的文獻基礎上不絕如縷地傳承下來。
出土文獻為我們打開了一道門,讓我們直接走向那個未經秦火的時代,中國文化的探源工程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據。“先秦古典學的重建”“古史的‘新探’或‘重建’”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系年》的價值
什麼是歷史文化的重大發現?對重大問題或填補空白,或顛覆常識。《系年》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當之無愧。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在那個時代有這麼一部書,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先秦史書。
《系年》全篇138支簡,每支簡背有編號,共3875字(包括合文與重文)。全篇原分23章,每章相對獨立,章尾有標志,簡尾留白。內容自武王克商開始,一直到戰國早期三晉與楚大戰、楚師大敗結束。《系年》的價值是多方面的,略作條述。
《系年》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前四章有關西周晚期與后四章戰國早期的史事。這是兩個處於歷史變革關鍵的時期,但史料奇缺,我們所知甚少。李學勤先生根據《系年》率先在《光明日報》上探討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響﹔課題組其他成員也有很多成果問世。中間15章雖然大部分可與《左傳》互証,但或異或同,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對更加准確認識那個時代有重要意義。隨著材料的公布,“古史新探”之類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為先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系年》的史書體例獨特,是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許兆昌教授指出,“其謀篇,布局宏大”,“縱觀各類傳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學文獻,《系年》應與《左傳》《竹書紀年》《國語》等史著一樣,代表了先秦史學創作的最高成就”。我完全贊同這樣的觀點。《系年》在先秦史學創作中還有其獨特性。全篇既不是單純的紀事本末體,更不是編年體,而是有整體布局,通過敘事與剪裁,表達著者的歷史觀。這種體例先秦史書聞所未聞。在與馬衛東教授談論《系年》時,他為那個時代有這樣明確“史學意識”的著作而驚訝。我相信,《系年》的出現,就像曾侯乙墓編鐘改變對音樂史的認識一樣,也會改變我們對先秦史學的認識。
古書的形制很早就有學者根據文獻上的一些記載做過梳理和推測,但未見實物,扑朔迷離。《系年》讓我們看到一部完整的古書。竹簡編號、簡背劃痕、分章、標點、篇題等等,信息豐富多彩,不僅讓我們目睹了先秦竹書的原貌,更為重要的是在竹書的整理過程中,形制對於竹簡的編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系年》的文字規整秀麗,最初我們以為是典型的楚文字,經過深入研究,發現不少字與楚文字的寫法或用法不合,有的保留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古老特征,有的字具有三晉文字的特點,這不僅涉及文本的來源、作者的身份等,而且讓我們對“楚文字”也重新思考。具備什麼樣的特征才能叫楚文字?楚文字內部的地域差異有多大?列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給楚文字帶來什麼影響?《系年》文字疑難字不是很多,但一些獨特的寫法和用法還是讓我們對一些文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並以此為契機,對一些構形不明的文字和歷史問題加以新的解讀。
楚簡字跡風格十分多樣,清華簡的字跡從整體上看以整飭規正為主,不同書手又表現出突出的個性,非常具有觀賞性,從藝術的角度看也很有價值。
作為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我們非常期望能夠對其作者、史料來源、創作目的、歷史觀念、文本流傳等有所了解。遺憾的是,這些重要信息即使留存也都被破壞,消失殆盡了。隨著清華簡的逐步公布,我們會對墓主的知識結構(也可以視作《系年》的知識背景)看得越來越清晰。
總之,《系年》是填補空白、改變常識的重大發現,有著多重價值,需要我們慢慢消化。